
印度漢學家狄伯杰。郭紅鬆/繪

《中印情緣》 【印度】狄伯杰 著 中譯出版社

英國漢學家凱瑞·布朗。郭紅鬆/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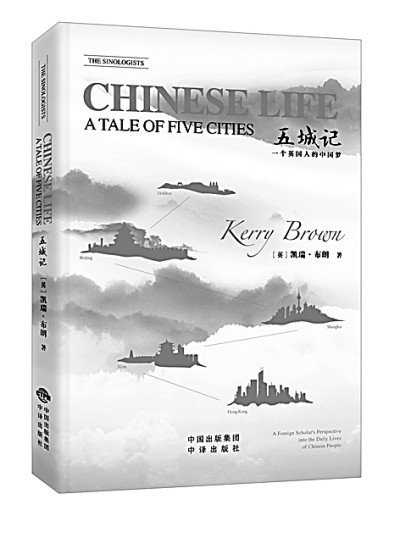
《五城記》 【英】凱瑞·布朗 著 中譯出版社

德國漢學家顧彬。郭紅鬆/繪

《顧彬唐詩九講》 【德】顧彬 著 商務印書館
編者按
似乎沒有一種比圖書更為合適的介質,能承載著一國的文明與文化,跨越國界,與萬裡之外的讀者悉心交流。它們安靜但富有深度,堅硬而內心柔軟,它們讓世界各地的心相通、意相融。因此,在又一個世界讀書日來臨之時,我們遍尋這樣的書籍,邀請它們的作者——來自海外的漢學家們來談一談他們的作品,講述他們如何與中國結緣,又如何通過自己的書寫,為跨越國界的文化交流增添一份色彩。
【新書訪談錄】
狄伯杰:人類文化由人類共同創造
印度中印關系專家、翻譯家,尼赫魯大學中國與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光明悅讀:您在《中印情緣》一書中,追憶了您的求學、教研和結識中國妻子的經歷。在這裡,您能否簡要向我們的讀者介紹您如何與中國結緣?
狄伯杰:中學時代,我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僅限於中國的長城和玄奘。在我為父親大聲朗讀的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中,我隱約記得,其中提到了般度族和阿薩姆王之戰的故事,后者得到了中國人的幫助。然而,有趣的是,我在童年時代聽大家所唱的描述中國的兩首流行歌曲,一首大概誕生於印中關系親和密切的時候,中國被視為一個富饒繁榮的國度﹔第二首歌和上一首歌描述的截然相反,它反映的是1962年兩國邊境沖突前后,印度與中國相互的敵意。在高中,由於我選擇學習歷史和地理科目,自然對中國的歷史和地理也頗有興趣。我從學校的圖書館借到了一本題為《東亞歷史》的書,不但有生以來第一次粗淺地接觸到了中華文明,而且還了解了其對諸如日本、韓國等一些國家的影響。可能也是第一次知道了長江、黃河。真正與中國的接觸始於我考上尼赫魯大學中文系之后。在譚中教授、葉書君教授、H.P.羅易博士、維姆拉·薩蘭女士和馬尼克·巴塔查裡亞博士的指教之下,掌握了中國方方面面的知識,尤其是中國歷史、文學、文化等。后來碩士畢業又到北大進修,學習了古代漢語、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印關系等科目。我和我的妻子是在北大芍園外的排球場上認識的。戀愛關系確定后,我們的話題更多了,我的中文口語也更好了。
光明悅讀:您在書中引用季羨林先生的話,呼吁印中兩國恢復以相互學習和理解為核心的“文明對話”。他曾說,“印度和中國是天造地設,因此孕育了兩種孿生文明”。在您看來,兩國文明有哪些接近性?
狄伯杰:我在北大念書期間,經常去打擾季羨林先生。我的博士論文,論題就是《印中兩國人民在反帝斗爭中的支持和同情》。當時,季羨林先生還贈送我他剛剛出版的著作《中印友好關系史》。其實如果仔細閱讀,能發現季先生的著作提倡的是“循環式”文化交流。這就涉及印中乃至周圍其他國家之間思想、技術、人文等的循環式交流。佛教經典、印度兩大史詩、神話故事、傳奇、變文、話劇的相互譯介,《道德經》等諸子經典的梵文翻譯,印中高僧的互訪,制糖、造紙、造絲等技術的傳播交流,都屬於這些范疇。因為我掌握了這方面的一些皮毛,就敢翻譯深圳大學郁龍余教授所著的《季羨林評傳》和《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印卷》。最近,后者的英文、印地語版都問世了。它們系統研究了兩國之間的循環式交流,指出印度與中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
光明悅讀:《中印情緣》是一本怎樣的書?它如何推進兩國文化對話?
狄伯杰:《中印情緣》(My Tryst with China:‘Our’ Footprints on the Sands of Time) 不僅描述了我自身的經歷,更記錄了印中交流史上偉大人物們的足跡。他們打通了印度和中國之間的交流渠道,推動了兩國的文明溝通。英文題目中的“我們”(our),包含了佛學發展巔峰及之后喜馬拉雅山脈兩側的諸多高僧﹔包含身處中國的季羨林、吳曉玲、金克木、劉安武、金鼎漢、王邦維、黃心川、林承節、耿引曾、薛克翹、王樹英、郁龍余、姜景奎等,以及身處印度的泰戈爾、柯棣華、師覺月、譚雲山、譚中、雷易(H.P.Ray)、葉書君(Yap Rahman)、沈丹森、瑪妲玉(Madhavi Thampi)等學者。他們持續照亮著兩種文明的對話之路,即便遭遇戰爭時期、蠻荒年代和地緣政治沖突,他們依舊維持著兩國人民心中的對話之火而不滅。中國的印度學泰斗季羨林教授認為,兩國的密切交流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中印文化交流史告訴我們,我們兩個國家在過去的兩千余年中互相交流、互相學習,發展和充實了彼此的文化,一直到今天我們尚受其益。這種交流,隻有好處,沒有壞處。
光明悅讀:您曾熟讀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領袖人物著作,也熱愛中國的古典和當代文學,游歷過西安、南京、揚州等古都以及上海等城市。您最希望把中國的哪一部分,介紹給印度讀者?
狄伯杰:我已經把《論語》《孟子》《四書》,陳來所著的《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以及《季羨林評傳》《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印卷》《我與柯棣華》等著作翻譯成了印地語和英文。因為有了印地語版、英文版,這些著作開始出現其他印度地方語言版本。除了上述著作外,我已經翻譯完了元曲《西廂記》《竇娥冤》,清代小說《儒林外史》,張煒先生的《古船》,這些書已經進入出版流程,不久就會問世。《紅樓夢》的翻譯,我也正在進行,還需要一段時間。此外我還幫助印度一些出版社出版過莫言、阿來、賈平凹等作家的著作。
至於最想介紹哪一個地方給印度讀者,我覺得我還想把西安和延安介紹給大家。
西安是古都。陝西歷史博物館所藏的文物,從商周的青銅器到熠熠發光的唐朝金器,數不勝數。公元652年修建的大雁塔內,存放著佛經和玄奘從印度帶來的佛舍利。公元645年,46歲的玄奘回到唐都長安,城內盛況空前,僧人們抬著他從印度帶回的657部佛經列隊而行。玄奘是真正的文化大使,踏上這位中國高僧曾經行走過的地方,讓人有一種激動人心的感受。
延安是中國革命的搖籃。1938年9月,印度國民大會黨向中國派出了一支印度醫療隊以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柯棣華醫生是醫療隊成員之一。柯棣華大夫參加了許多戰斗,1941年他正式加入了八路軍,不久被任命為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長。他志願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名戰士,努力學好中文,培養了數百名醫生和護士。很有幸,我成為他的妻子郭慶蘭所撰寫的《我與柯棣華》一書的譯者,她在致我的一封信中說,“祝中印兩國人民的友誼似喜馬拉雅山一樣萬古長青,似長江、恆河一樣永遠奔騰不息!”我想,這也是我的期待。
凱瑞·布朗: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與我家鄉的人相差無幾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劉氏中國研究院”主任,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亞太項目高級研究員、亞洲項目負責人
光明悅讀:您在《五城記》的序言中追溯,您在英國所接受的公立教育體系,包括在劍橋大學的學習過程中,幾乎不見任何關涉中國的內容。您是從薩義德東方學的知識體系裡,開始了解“遠東”。在英國,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彼此相互隔絕的狀況,持續了多少年?大約從何時起,中國開始“存在於”英語世界裡?
凱瑞·布朗:我在英國東南部的肯特郡接受了中小學教育,之后就讀於劍橋大學,先修哲學,后習英國文學。這段時期,我的興趣囿於西方傳統之內,希臘哲學、洛克(Locke)和霍布斯(Hobbes)等英國思想家、維根斯坦(Wittgenstein)和康德(Kant)等歐洲思想家,構成了此類教育的主體。在我中學的圖書館,唯一與中國相關的書籍是一本孔子《論語》的平裝版,對於一個十五歲的學生來說,這本書令人費解。我在青年時代,讀到過一本法國學者雅克·格奈特(Jacques Gernet)寫的關於中國文明的大部頭著作,我盡力加以研習,可是,該書所涉及的時間軸以及對歷史的敘述,似乎均無法與我熟悉的歐洲時間軸以及歷史敘述形成任何關聯,中國的歷史似乎是一種全然不同於歐洲的時間感和敘事。我覺得直到現在,西方和中國某種程度上仍然存在著“隔絕”狀態。
最近幾年,我所觀察到的變化有兩個:一是貿易上中國制造的產品越來越多地銷售到了英國﹔二是英國本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中國游客和留學生。這代表了中國“進入”英國的一些方面。從某種程度上來講,英國與中國在互動上仍然處於較為被動的狀態。目前這個狀況沒有很大的變化。我最近正好在寫一本歐洲過去800年來文豪與哲學家等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這本書預計於今年夏天以中英文同時出版,裡面詳細地描述了近800年來歐洲文人與中國的交往,以及歐洲對中國的印象變遷。
光明悅讀:能否請您介紹,您如何與中國結緣?
凱瑞·布朗:我從劍橋大學畢業之后去日本工作了一年,在那期間,大概是1991年5月,我坐飛機從大阪出發,經上海到北京,旅行了一周。那時去中國很不容易,那次旅行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欣賞中國文化和現代歷史的機會。中國帶給我一種出乎意料的感受,既大不相同,卻又十分熟悉。中國“無法為人所知”、極度神秘莫測的觀念開始遭受挑戰。我發現,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芸芸眾生,與我所來自的地方的人相差無幾,人們努力地過好屬於他們自己的日子,每天忙忙碌碌地操持著各自的事務,與我家鄉的情形甚為相似。從那時候我開始學習中文。在系統學習一年中文之后,我在1994年抵達內蒙古,在那裡的醫學院度過了兩年的時光。那兩年給了我真正在中國生活的經驗,從那時起,我就覺得我是半個中國人了。
光明悅讀:在撰寫《五城記》之前,您撰寫了大約20余本關於中國的書,它們關乎哪些類型?《五城記》是一本怎樣的書?
凱瑞·布朗:有一部分是關於中國近代史,一部分是關於中國政治與經濟,還有一些是關於中國外交。
《五城記》是一部自傳,是我在中國工作和生活,親歷的關於呼和浩特、北京、上海、西安、香港五個城市的故事。呼和浩特是我最初了解中國的地方,我在書裡寫了它的飲食、城市布局、大學生活、歷史,寫了英國詩人柯勒律治(Coleridge)詩歌裡的“夏都”在當下是怎樣的狀態。北京是一個開放、宏偉的政治中心,我寫了我的外交官生活,寫了紫禁城、長城、公園,寫了在北京生活衍生的哲思,我還寫了北京的傳統與現代。上海是中國的商業中心,我寫了外灘、建筑、新金融中心,以及它的友好城市之一利物浦與它的交往,書中有我對以上海為代表的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思考。西安,是唐代的首都,我寫了它的博物館、大雁塔、半坡遺址等古跡,以及這座城市沉澱的意義。至於香港,我寫了它的日與夜,以及我造訪它時所帶有的情感負擔。
在書裡,我將我所知道的中國“和盤托出”,將中國的“不可知性”以及如何超越這種“不可知性”轉化為一個中國故事,盡量將故事講得坦誠,實事求是。本書所說的,總體而言,是原本的英國夢如何在我身上轉而化作了中國夢的故事。
光明悅讀:《五城記》,能為西方讀者了解中國提供怎樣的經驗?
凱瑞·布朗:這本書以中文版和英文版兩個版本同時出版,是給中國人看一看英國人眼中在中國的生活,也給英國人看看一個英國人在中國怎麼生活。我覺得,書本提供的最重要信息是,如果不了解中國文化,就不可能了解中國這個國家和中國人民。我們必須找到共通的地方,比如英國人特別喜歡文學,中國人也為他們的文學感到自豪。英國人和中國人雖然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們也有許多共同之處。好像中西方現在很容易找到對立面,但我在寫書時,最重要的任務是在其中找到雙方的共同點。
光明悅讀:您在《五城記》中簡要比照了莎士比亞與曹雪芹,說他們都擅用暗喻。他們二人及其文學作品有哪些相似性?能為人們的精神世界提供哪些觀照?
凱瑞·布朗:我的朋友們認為,他們喜歡的是《紅樓夢》中的語言、隨處可見的引用和典故,以及文字間隱含的寓意。莎士比亞的創作與此類似,他筆下的許多戲劇並非隻有敘事,他的語言豐富多樣,讀者通過語言可以感受其中不同深度和廣度的情感表達。書中我還簡單比照了《追憶似水年華》和《紅樓夢》,作為文化的平行文本,它們在各自的國家擁有極高的威望和地位。據我所知,《紅樓夢》有大量的對話和對一座園子裡跌宕起伏的人物關系的描寫。《追憶似水年華》有大量關於派對、大型宴會和群體討論中人們互動的描寫。雖然曹雪芹和普魯斯特的創作方式不同,但他們的目的類似,都是通過小說語言的內部隱喻和情景化處理,讓故事的內容比表面看上去豐富得多。
顧彬:唐詩可與西方哲學互文,唐詩屬於世界
德國漢學家、翻譯家、作家,波恩大學漢學系終身教授
光明悅讀:您的《顧彬唐詩九講》一書近日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一本從德國當代哲學視角來解讀中國唐詩、甚至中國文學的書。您能否簡要向讀者解釋,運用這一視角您有什麼樣的發現?
顧彬:有中國學者曾說,我用德國當代哲學的視角來解讀唐朝詩詞,就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做法。其實,在其他學科領域,我也早已做過這樣的嘗試。2011年到2019年,我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古代哲學。我在德國Herder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思想家叢書”一共有10卷,是用德國20世紀哲學提出來的問題,來解讀孔子、庄子等中國思想家。
既然,古老的東方哲學可通過德國當代哲學視角與讀者相見,那麼,唐詩有何不可?人們往往認為,唐代文人對人的存在等問題的思考,跟我們今天的考慮完全不一樣。然而我發現,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中國,古人與今人的思維方式仍然有很多共同點。簡單地說,這是人的存在的一個基本特點。德國理想主義哲學代表人物之一謝林(Schelling),第一次從人的渴望視角來看待我們的生存。有不少德國當代哲學家繼承他的“衣缽”,發展這一理論體系。我發現,這一理論,即使在遙遠的中國唐代,也能從詩歌中找到存在的証據。如李白的《烏夜啼》,描寫了女人與窗的關系,這就是盼望,希望丈夫早日歸家。德國畫家(Caspar David Friedrich) 畫過很多女人透過窗戶看外面的畫作,表達的是相同的渴望。將視野延伸得更廣闊一些,我們可以從杜牧的《赤壁》中讀到“偶然性”,從李商隱“來是空言去絕蹤”裡讀到“等待”,從王維《竹裡館》裡讀到“孤獨”,從白居易《耳順吟寄敦詩夢得》裡讀到“放鬆”……這些都是德國當代哲學熱衷討論的重要話題,我們可以從一個遙遠的東方國度的古老詩歌裡找到証據。
最為重要的結論是,如果我們能從歐洲哲學的視角來理解唐詩、思考唐詩,這不是恰恰說明了——唐詩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嗎。
光明悅讀:在書中您提及,大約在20世紀60年代,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您接觸到了李白的詩歌,於是您開始學習漢語。后來您放棄了自己原來的專業,選擇漢學作為主業。能否講述,自那時開始您與漢學、與中國結下的緣分?
顧彬:我從很久以前開始,就開始尋找“人”,尋找人存在的意義。我最先學習的是哲學,然后轉念神學。不過,我從大學開始上神學的課程時,我仍然找不到“人”。很偶然的一個機會,一位來自漢堡市的年輕詩人給我介紹了孟子、李白等東方先賢,我覺得我應該學一點古代漢語。我似乎一下子,從東方古老的哲學與詩歌中,找到了“人”。當時我憑我的直覺,從神學轉學漢學。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的選擇是正確的。目前,以我的觀念來看,仍然是中國古代哲學與中世紀的詩詞教會了我,我們人的存在是什麼。
光明悅讀:您的博士論文是《論杜牧的抒情詩》,在波恩大學任教期間,主編了10卷本的《中國文學史》,並撰寫了其中《中國詩歌史》一卷。您能否介紹,中國文學在德國的傳播情況?
顧彬:提到這個,我的心血在流。在中國文學翻譯、介紹方面,德國曾經有過很強的優勢。無論是哪一個時代的文學,雖然我們的翻譯家人數很少,但是一百多年來,我們什麼都翻譯過、介紹過、書寫過,一些著作的出版比美國要早得多。但是我們目前面臨一個很大的危機。德國大學的漢學,研究重點基本上從古代轉到了當代,從文學轉向了經濟、政治。目前還在翻譯、研究中國文學的人,跟我一樣都是退休的老教授或者大學之外的學者。當然,我是波恩大學的終身教授,每個學期還是會給學生上課,但是自從我2011年到了北外、2019年到了汕頭大學以后,我都在德國之外的中國國內教授中國文學、哲學。我認為,中國文學有獨特的魅力和價值,值得繼續研究。
光明悅讀:您認為,中國與德國最主要的文化差異是什麼?您在撰寫著作時,試圖怎樣去增進對話?
顧彬:從哲學視野來看,沒有差異。你們比我們懂馬克思!懂德國人。不光是研究馬克思的學者,研究其他哲學家的中國學者,也有很多來德國的學術場合進行公開討論。學術的交流,沒有國界。我們去年不是修繕了恩格斯故居嗎,故居對面就是中國贈送的雕塑。我和我的學生去過、看過、談論過,其中也包括很多來自中國的學生。
光明悅讀:在您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的50余部專著、譯著中,有六卷本的《魯迅選集》,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和《寒夜》,您也譯介過當代詩人北島、翟永明等人的詩歌。如果選擇一位唐朝詩人譯介紹給德國讀者,您最希望介紹的是誰?為什麼?
顧彬:有時我開玩笑地說,我年輕的時候愛李白,老了之后就愛杜甫。我翻譯過詩人王家新、西川的作品,他們滿口都是杜甫的名字,他們也老了。我們老了之后,開始有了很多思考,原來想過李白似的生活,想多喝白酒,但是現在要少喝。西川老在路上尋找杜甫,王家新老是在紙上跟杜甫打個招呼。我呢,我還是愛李白。杜甫是地上的,李白是天上的。我也想跟他們見面,故去之后我不是可以上青天嗎。李白是天空的仙人,我還是想學他。(韓 寒)
飛向藍天的“卓瑪”(身邊的小康故事) “卓瑪,飛機能飛多高啊?”“卓瑪你去過哪些城市了?”……每次回家,格茸卓瑪仿佛是村裡的“明星”。 格茸卓瑪的家鄉在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裡拉市小中甸鎮團結村。這個很多人沒有坐過飛機的村子,卻走出了一位在飛機上工作的女孩。 作為東航…【詳細】
雲南新增19例境外輸入確診病例 人民網昆明7月27日電 (符皓)據雲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通報,7月26日0時至24時,雲南無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例19例、無症狀感染者3例。確診病例治愈出院2例(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解除隔離醫學觀察2…【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