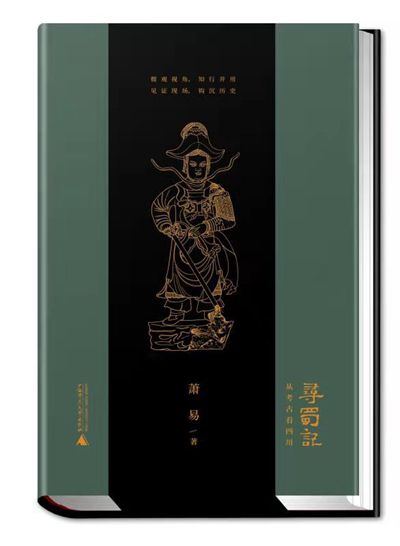
三星堆遺址近日新發掘6座“祭祀坑”,一時萬眾矚目。很多人說,四川的歷史文化,太適合用考古模式打開了。而長期關注四川文化的作家蕭易,最近出版《尋蜀記:從考古看四川》。讀完后感覺,這不就是一本用考古現場解鎖四川版圖的書嘛!
一個個震撼世人的考古現場,在書中扑面而來:先秦時代的寶墩古城、三星堆青關山遺址、金沙遺址、蒲江戰國船棺葬,南北朝的萬佛寺遺址,唐代樂山大佛及其“哥們兒”,宋代的瀘縣宋墓、彭州金銀器窖藏,明代王璽家族的報恩寺、張獻忠江口沉銀,清代鹽亭的字庫塔……
《尋蜀記》並不限於一本作家書寫的旁觀蜀地考古手記,“尋”的意義和分量顯然更重,作者試圖用考古模式打開四川,或能為史書記載補上諸多缺失的歷史拼圖。
大眾熟悉的歷史,往往是以通史的方式書寫。而在史書記載中,屬於四川的記載篇幅並不充分,甚至可以說地位有些“邊緣”。傳說中,古蜀國經歷了五世蜀王,而具有代表性的、正面描述古蜀歷史的文獻記載,隻有西漢揚雄執筆的《蜀王本紀》,以及東晉常璩所著的《華陽國志》,提到古蜀國最初幾個王朝更迭的大致輪廓。
持續多年的考古發掘工作,正在努力破譯古蜀文化的密碼。
寶墩古城是中國史前第四大古城,如啟明星一般照亮文明前夜的成都平原,有力証明了成都平原也是文明的重要源頭﹔廣漢三星堆的持續考古發掘,給神秘的古蜀文明逐漸揭開面紗﹔金沙遺址共出土金器200余件,為商周時期古遺址出土金器最多,該遺址的考古告訴后人,三星堆文化消亡之后,在成都平原又誕生了另一個高度發達的文化……
古蜀文化的演變,經歷了從寶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古蜀大型船棺遺存的發展脈絡,與古蜀國傳說的“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大致相當。
再以漢朝蜀地歷史為例,從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這中間延續400多年的漢朝歷史,史書分配給蜀地的章節非常有限。直到今天,大眾對於漢代蜀地的了解,大多停留在“列備五都”“錦官城”“文翁興學”“文君當壚”等關鍵詞上。
“可以想象,大漢王朝的每一個郡,每一個縣,每一個鄉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會有無數故事發生,只是未進入史學家的視野,自然也就鮮為人知了。”蕭易試圖從微觀的剖面,解讀蜀地歷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它的故事,則來源於被史書遺忘的片段和角落。
大漢王朝的邊陲,北方絲綢之路沿途分布著樓蘭、龜茲、烏孫、焉耆等諸多古國,而在西南,昆明、邛人、笮人、滇人、夜郎等部族,則分別把持著廣袤的土地。此前我們對於這些部族的了解,來自司馬遷的《史記·西南夷列傳》:“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
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史記》中“西南夷”被考古發掘証實。“那些消失的部族,向后人展示著自己的戰爭、外交,乃至對死亡的態度。安寧河流域矗立著兩百余座大石墓,由重達數噸、數十噸的巨石壘砌而成,墓中尸骨累累,史前的邛人部落對死亡極為敏感﹔笮人則是些狠角色,老龍頭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銅兵器”。
因為考古,今人一點點拼湊對蜀地的認知版圖。而當我們把目光聚焦到單個文物的“前世今生”時,仿佛偵探破案現場,蜀地每件文物出現的坐標,及其表面殘留的痕跡,都給了今人大量線索來回答塵封已久的問題:我的主人是誰?他(她)何時擁有了我?他們后來去哪兒了?
《尋蜀記》提到,彭州窖藏金銀器350件,是中國迄今為止最大的宋代金銀器窖藏。而四川總體窖藏金銀器近500件,約佔中國宋代出土金銀器一半。而作者講述的著力點,在於董氏家族的悲歡離合。
《尋蜀記》“西蜀夢華”一章,開篇就是一個讀來頗為唏噓的場景:大約在南宋端平年間(1234-1236)的一天,夜深的成都府彭州城,董宅的燈還亮著,董家老老少少面色凝重,因為他們已經聽說蒙古人從大散關打來,每到一處就燒殺搶掠甚至屠城,恐怕不久便打到彭州。
倘若蒙古人殺進城,不但家中財產難保,連性命都堪憂。董家眾人商量再三,決定將金銀器挖坑埋藏,暫避風頭。董家人挖了一個長1.2米、寬0.8米、高0.9米的大坑,掩埋了財物。城中另一戶驚慌失措的人家也做了同樣的事,埋藏了家中的仿古青銅器,但如今已不能確認這戶人家身份。
之后,董家人便踏上了流亡之路,戰爭硝煙彌漫,四川生靈涂炭,他們再也沒有回來。藏於地下的這些金銀器,沒有等到主人,而是沉睡了八百年之久,直至1993年才重見天日。
在考古學中,為了躲避災難而藏匿財物的遺址,被稱為“窖藏”。蕭易還特別提到一位“董小姐”的首飾,簪身、釵身彎曲的折痕,似乎能夠說明曾被經常使用。蕭易感慨戰爭的殘酷,“精美的窖藏被塵封在地下,同樣被塵封的,還有宋人奢華精致的生活——推杯換盞、觥籌交錯”,沉靜的文物,可以在黑暗中等待和穿梭數個時代,而一個人的存在和愛恨,何其短暫、縹緲。
當蕭易來到張獻忠江口沉銀遺址時,圍堰裡的江水已被抽干,裸露出大片的砂石。砂石運走,鵝卵石和泥沙之間,顯露出八大王的珍寶。“這些金首飾還蘊藏著許多信息,金鐲子曾被掰彎,並有燒灼痕跡,許多戒指、耳環出水時即串聯在一起。顯然,大西國的將士曾試圖將它們扭曲、熔化,以便於攜帶。”
蕭易看到擺出來的金銀器,萌生出了與很多人不一樣的思緒:“那些成堆的銀首飾,由於尚未來得及清理,它們被分門別類堆放在塑料箱裡,其數目何止成百上千。這些耳環、戒指顯然來自無數個朴素的明代家庭,城破之日,它們的主人被迫交出畢生的珍藏,爾后消失在無休止的戰亂中。30000余件文物,每一件背后,或許都是一出悲劇。”
每一件文物,都寫著一個人命運多舛的一生。他們不曾在史書上留下名字,他們的悲歡被掩埋地底、淹沒水中,最終消失在一個朝代或地域的盛名之下。
今天我們看見蜀地的那一件件文物,可以視其為古人那一雙雙凝視的眼睛。這些眼睛告訴我們,歷史之河從哪裡流淌而來,要往何處奔流而去。考古事業的意義之一也在於此,時間永不停歇,人類一直存在,我們背負著全部歷史,向前。(記者 沈杰群)
飛向藍天的“卓瑪”(身邊的小康故事) “卓瑪,飛機能飛多高啊?”“卓瑪你去過哪些城市了?”……每次回家,格茸卓瑪仿佛是村裡的“明星”。 格茸卓瑪的家鄉在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裡拉市小中甸鎮團結村。這個很多人沒有坐過飛機的村子,卻走出了一位在飛機上工作的女孩。 作為東航…【詳細】
雲南新增19例境外輸入確診病例 人民網昆明7月27日電 (符皓)據雲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通報,7月26日0時至24時,雲南無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例19例、無症狀感染者3例。確診病例治愈出院2例(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解除隔離醫學觀察2…【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