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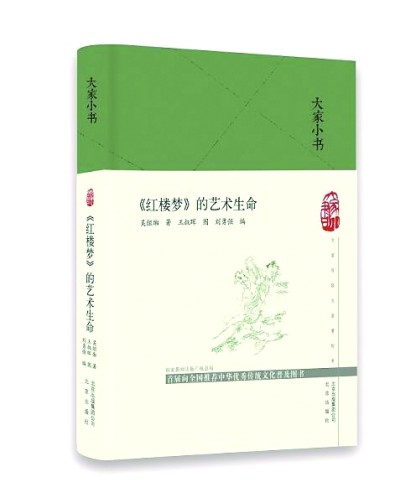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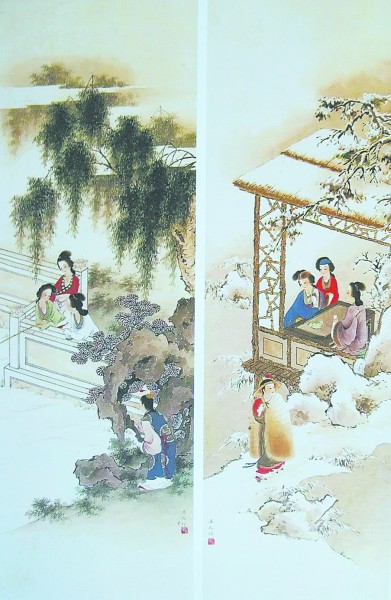
紅樓人物畫:寶玉促狹(左),寶玉踏雪(右) 王叔暉繪

黛玉葬花(唱片封套) 王叔暉繪
吳組緗出生於1908年,是中國現代著名小說家、學者。他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與林庚、李長之、季羨林並稱“清華四劍客”。1952年起他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潛心於古典文學尤其是明清小說的研究,曾兼任《紅樓夢》研究會會長等職。吳組緗對《紅樓夢》的研究在紅學界產生過廣泛影響。今天重溫他關於《紅樓夢》的深刻觀點,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這部偉大經典名著。
20世紀70年代末的北京大學,王力、林庚、吳組緗等老先生重登講台,一個個抖擻精神,開講他們的課程。在新的歷史時期,他們與我們這批學子邂逅了。這是隔代的傳承,三生有幸。
那時候,教室沒有空調,沒有擴音設備,課堂常常人山人海的,聽不清楚,有時連先生的身影也瞅不見。后來,王力先生的弟子給我們班上小課。而林庚先生的《楚辭》課、吳組緗先生的《紅樓夢》課,我是后來自己找書來看,補齊的。
近年我應邀做了幾回《紅樓夢》講座,發現青年讀者特別迷戀於“神話”“判詞”等意象,喜歡先入為主,帶著情緒閱讀,而對其社會內容卻隻論皮毛,鶯鶯燕燕、視野狹小,忽略了這部名著廣闊的社會背景和最寶貴的那一股“人性抗爭”的精神。
這使我想起了吳組緗先生當年曾對越劇《紅樓夢》的批評:
主要的問題是把它抽出來了,成了個才子佳人戲。才子佳人,一見傾心,后面加上了傷感主義情緒的宣揚,叫人家哭啊。實際上沒有多少社會內容了,比原來的作品差得遠。(《吳組緗:《關於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的幾點體會》)
“寫出了造成這個悲劇的全面的深刻的社會根源”
《紅樓夢》這部小說的“社會內容”分量,遠非是詩詞意象可以承載的。很多學者是認可《石頭記》這個書名的。全書以“石頭”“石兄”的角度和語氣開端,巨著最先的成形,是以“石頭”為主角的小說,線索分明,故事頇實,個性鮮明。主干是“木石前盟”,即寶黛戀愛事,悲情動性。而《紅樓夢》這個書名,是從賈寶玉在“太虛幻境”聽曲而來的。賈府與大觀園中,並沒有什麼顯要的樓,綴錦樓很平淡,天香樓浮光掠影。用這十二支曲名來作小說的名字,其實是名不符實的,難以涵蓋。這曲唱“女兒”的命運,可小說並不隻寫了“女兒”。
從創作的角度看,在已經有了大本的故事后,為了讓“金陵十二釵”也有個“來歷”,好與“絳珠草還淚說”匹配,作者在第五回才設計出了“太虛幻境”。“太虛幻境”四字拆開來,每一個字都意味著“虛無”,全書中也隻有賈寶玉一個人神游過。他生下來就帶美玉,是最具神秘氣質的一個有“跨界”能力的復雜體:
於是賈寶玉這一高度現實主義藝術的典型形象出現在我們讀者之前的時候,被作者點染了許多神秘主義的迷霧。(吳組緗:《論賈寶玉典型形象》)
吳組緗先生在分析《紅樓夢》時,因為自己有小說家的實踐體驗,所以他對神話、“幻境”與“判詞”一筆帶過,而對人物的性格分析,則在其社會性和人生經驗上大下功夫。
魯迅說《紅樓夢》是“悲涼之霧,遍被華林”,我以為與吳組緗說的“神秘主義迷霧”相關聯。“迷霧”和“悲涼之霧”是一回事,指的就是那些神話、“幻境”與“判詞”,隱喻與暗示。“華林”則指貴族生活的實體社會。
“石頭記”是小說主干,“紅樓夢”是唱曲點染,辨析這兩個書名,其實已經點出了這部書的風格與寫作奧妙。
吳組緗先生說,作者為了構置林黛玉進入賈府的線索,預先寫賈雨村。重要的一點,是為了布局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三個中心人物的會合。(吳組緗:《談〈紅樓夢〉裡幾個陪襯人物的安排》)
寶黛由賈母安排,同居於隔室中,耳鬢厮磨,青梅竹馬,前景是大家庭中常見的姑表結親模式。《紅樓夢》描寫寶玉黛玉從“兩小無猜”到“兩大有猜”的過程,寫他們不斷地慪氣吵架,直到老祖宗說出那個“不是冤家不聚頭”的名言,才各自琢磨,明白了他們已經成為彼此“不可取代的那個人”。
對寶黛愛情成長過程的細致描摹,是中國小說對世界文學的一個貢獻,卻至今未被注意到。歌德寫《少年維特之煩惱》,以寫少年成長的青春糾結而成名,而《紅樓夢》則是東方生活的寫照。維特很快就舉槍自盡了,寶黛的故事卻涵納了豐富的社會內容。
《紅樓夢》的特點是,它寫出了這個悲劇發生和發展的復雜細致的現實內容,寫出了造成這個悲劇的全面的深刻的社會根源。這就是,一方面,作者不是簡單地或表面地了解賈、林、薛的婚姻事件,而是從悲劇主人公的思想性格上來看那內在深處的真相,從日常生活活動中來看那多方面的內心精神的關系的﹔另一方面,作者不是把問題局限在本身的范圍裡面,使之和所在的環境絕緣,而是圍繞著這個中心事件,同時鋪開了一個由無數有關人物所構成的極其廣闊的社會生活環境,亦即同時描寫了這個步步走向崩潰的貴族統治階級社會的真實內幕的﹔總之,作者是努力從人物性格和生活環境的極其復雜深邃的關聯和發展上來連根地“和盤托出”這個悲劇的。(吳組緗:《論賈寶玉典型形象》)
黛玉父親猝然去世,她失去權勢的支撐,門戶變得“不對稱”,使這件早先蓄謀的婚事發生變故。當衰落的賈府上下為薛家的炫富迷離,黛玉代表的“書香”卻走向式微。這是“步步走向崩潰的貴族統治階級社會的真實內幕”。
愛情成為才女的生命支柱。寶玉在多次詩社活動中,總是一力推舉黛玉的詩,這是文學與人生的雙重知音,表明寶玉有識才的慧眼,並非不學無術之輩。而黛玉的清高自許,從來不說那些“仕途經濟”的“混賬話”,更為寶玉所敬。
吳組緗先生分析寶玉對“女兒”的看法,從絕對的肯定,到發現“女兒”也有功利和清純的分野,從而堅定了他對林黛玉不可取代的愛情。寶黛皆有“真摯不事虛偽”的性格,這是他們相知相愛的基礎,也是他們區分於眾人的鴻溝。
讀小說,覺得薛寶釵“來路”很不自然,不像林黛玉,年幼喪母,投奔天倫,召喚出合府人的親情之嘆。而寶釵入府,上下送禮,收買人心,是有攻略的。
初會時,寶玉“問玉”,黛玉說,“我沒有玉”,何等坦白。寶釵卻在寶玉來訪時,提出“看玉”,又“讀玉”,引起金鎖的話,與丫鬟配合,扭扭捏捏,是排過的劇本。
這是“從日常生活活動中來看那多方面的內心精神的關系”。
吳組緗先生說,寶釵入京“待選”才人、贊善,看似順便交代,其實作者就是在貶薛家之不堪的。在封建時代,一般善良的父母都不肯把自己女兒往深宮裡送,犧牲女兒的終身幸福來謀求富貴。他舉出《聊齋志異》的故事和川劇《拉郎配》為例子,說:薛家卻不是這樣的。
吳組緗先生是在用一種廣泛的歷史常識來分析《紅樓夢》的人物個性。
薛家在京中有很多房子,本來完全可以住到自己家裡去,俗語說“探親不如訪友,訪友不如住店”,自己家裡有漂亮的房子,為什麼非要跑到賈家去住?而且簡直是賴著不走!(吳組緗:《賈寶玉的性格特點和他的戀愛婚姻悲劇》)
《紅樓夢》中屢屢提到薛寶釵一家住在賈府的曖昧處境。雖然賈政與賈母都說著挽留的話,但並不在情理之中。直到元春宣布,眾姐妹入住大觀園,才給了薛寶釵一個“合理性”。元春用心甚深,給寶釵的才具施展創造了廣闊空間。而寶黛離開賈母的居所,也就離開了祖母的庇護。
20世紀50年代,吳組緗和何其芳同在北大開《紅樓夢》課,觀點有別,如唱對台戲。比如,吳組緗不同意何其芳說薛寶釵是“封建淑女”,認為她城府很深、工於心計,有很明顯的市儈習氣,是一個實利謀求者。“金玉良緣”之說,是“迷霧”,不是情感緣分。寶釵原為“待選”而來,未遂,轉而謀劃寶二奶奶之位。這與寶黛之情地老天荒,不可比擬。
第六十七回“見土儀顰卿思故裡”一開篇,說尤三姐烈死,柳二郎“心冷入空門”后,薛姨媽不知為何,心甚嘆息……
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日媽媽為他救了哥哥,商量著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隻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
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作者寥寥幾句,描出薛寶釵這個“冷美人”的無心無腸。到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一筆兩處,寫賈寶玉痛失摯友、痛惜紅顏的悲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奈寶玉因冷遁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連連接接,閑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痴,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疾。”而日后卻偏偏是冷漠的薛寶釵成了情重的賈寶玉的妻子,用這些鋪墊的細節點出了“金玉良緣”的空洞冷酷。這是“從悲劇主人公的思想性格上來看那內在深處的真相”。
“但作者並不追求這個,他要寫神似”
《紅樓夢》女性,凡名字含優美意象的,都是曹雪芹喜愛的人物。如:黛玉、晴雯、湘雲、岫煙,是“第一流”的,有詩意、氣象和無盡的想象空間。書中用“霽月難逢,彩雲易散”“湘江水逝楚雲飛”“千裡東風一夢遙”等等判詞意象的事先點染,造就“悲涼之霧”,使人物故事未雨綢繆,渲染不祥之兆。寶釵、金鶯、金桂之類,世俗意味濃,這類人物基本沒有悲涼氣質。
黛玉葬花,可以看作是“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的詩畫合一的升華。“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此詩一出,使暮春天氣中的大觀園籠罩在一片淒慘的哭泣中。寶玉出現,與黛玉共情,並消解了他們昨夜的誤會。
作為小說家,吳組緗敏銳地覺察出,這段故事有些蹊蹺:“比如《紅樓夢》中寫林黛玉葬花,隨口就念出葬花詞來了,你說生活中有這種事情嗎?她在家沒有打底稿啊?形似上就差勁了。而且這首詩寫出來並不是林黛玉嘴頭上談出來的,她在那裡葬花,邊哭邊念,賈寶玉隔了好幾個石山,隔了一段路聽她哭哭啼啼地念,聲音很低,她念出來他就把它寫下來了。這就更不可解了。”
看到這裡我忍俊不禁,吳先生真是可人,學問大家都是尊崇自然與天然的。所以讀書還是要有一顆童心,才能切入。
多數人看黛玉葬花,都是憐香惜玉,有誰會想到這個情節在小說中是不合情理的。
但作者並不追求這個,他要寫神似,寫林黛玉的精神世界,寫她憐花,寫在這個狀態之下賈寶玉不理她,她格外感到身世孤微,就憐花,所以黛玉葬花抓住她那個精神,內心那個要點,把它構成一個畫面。(《吳組緗:《關於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的幾點體會》)
吳先生稱之為作者的“得意忘形”。他認為,寫到這裡,曹雪芹脫出了小說與生活的形骸,盡情抒發,精神翱翔。
來比較一下后面第七十六回“凹晶館聯詩悲寂寞”,湘雲與黛玉對出“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詩魂”,被妙玉走出來打住,三人同去櫳翠庵把聯句寫下來,這就是小說細節。而“葬花吟”的場景則是一種神游,是寶黛兩個靈魂的相遇。
讀小說,要像吳先生那樣實心實意,運用自己的生活經驗。
林黛玉這個人物是有歷史原型的。我曾看過一個明代才女葉小鸞與眉子硯的故事。
葉小鸞,蘇州人,自幼由姨母家撫養成人,后隨父到金陵,在出嫁前猝逝,未婚夫因而出家。她的詩詞《返生香》中出現“含顰”“愁黛”“葬花”等字樣,評家以為“較勝於朱淑真”。此女性格高曠,厭繁華,愛煙霧,視金錢若污物。
這些性格與經歷,正是小說的元素,黛玉有似歷史人物葉小鸞。而在小說內部,則常有“晴為黛影”的說法,指黛玉和晴雯除了外貌上有些相像,在品行上也有些類似。《芙蓉女兒誄》與《葬花吟》並舉。第七十八回“老學士閑征姽婳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賈寶玉應付完父親,回到怡紅院,有意避開麝月等人,留下兩個小丫頭,走到山石后面,向她們打聽晴雯臨終的情形。
小丫頭道:“回來說晴雯姐姐直著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也出不得一聲兒,隻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丫頭子說:“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淚道:“還叫誰?”小丫頭子道:“沒有聽見叫別人了。”寶玉道:“你糊涂,想必沒有聽真。”
這是晴雯臨終的真實情景,卻讓寶玉感覺到巨大的失落,難以接受。旁邊那一個小丫頭最伶俐,聽寶玉如此說,便上來說“真個他糊涂”。又向寶玉道:“不但我聽得真切,我還親自偷著看去的”。
小丫頭說晴雯是“受了委屈出去”的,算她看明白了這裡頭的奧秘。所謂“人知道,回了太太”,可以回太太的,隻有襲人,與寶玉心中不謀而合,於是這個丫頭繼續跟進:
誰知他平生為人聰明,至死不變,他因想著那起俗人不可說話,所以隻閉眼養神,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拉我的手問:“寶玉那去了?”我告訴他實情。他嘆了一口氣說:“不能見了。”我就說:“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豈不兩完心願?”他就笑道:“你們還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敕命我去司主……”
寶玉忙道:“你不看書識字,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一個神,一樣花有一位神之外還有總花神。但他不知是作總花神去了,還是單管一樣花的神?”這丫頭聽了,一時謅不出來。恰好這是八月時節,園中池上芙蓉正開。這丫頭便見景生情,忙答道:“我也曾問他是管什麼花的神,告訴我們日后也好供養的。他說:‘天機不可泄漏。你既這樣虔誠,我隻告訴你,你隻可告訴寶玉一人。除他之外若泄了天機,五雷就來轟頂的。’他就告訴我說,他就是專管這芙蓉花的。”
寶玉作《芙蓉女兒誄》,在小說中分量極重,誄文指出迫害晴雯的是“悍婦”與“诐奴”。而這篇文章的起由,卻出自一個小丫頭的信口編造,“花神”的來歷是她的“見景生情”。這也道出了《紅樓夢》中一切“女神”奧義,“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時有還無”。
一本《紅樓夢》,夭折的少女甚多。為何要“重祭”晴雯?
作為怡紅院中的大丫鬟,晴雯不圖月份錢,不像麝月、秋紋那樣羨慕別人的小便宜﹔不求“姨娘”的位置,雖明知襲人的處心積慮,卻坦坦蕩蕩行事。她原本是賈母選中來陪寶玉的,人才針線出眾,但卻保持了一身清白。最后遭污蔑,尸骨未寒被火化了。這是一個出色的下層少女的真實悲劇。
“高標見嫉,閨幃恨比長沙﹔直烈遭危,巾幗慘於羽野。”晴雯這股“女兒”的冤氣,在誄文中被比作受打擊被貶到長沙去的賈誼,救洪災反被殺在羽野的鯀。在曹雪芹看來,小人物的這口不平之氣,與大人物們的氣概是同等的。
讀者們不一定能記得和讀懂那篇冗長深奧的誄文,但對晴雯超凡脫俗的行為,“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拼病體“夜補孔雀裘”,和那些尖酸刻薄又義正詞嚴的話,在抄檢大觀園時從病榻掙扎起來,將箱子傾倒一地極盡憤怒與蔑視,音容舉止,印象深刻,不可與其他人混淆。晴雯的傲骨俠氣破書而出,這是小說刻畫的功勞。《紅樓夢》所有情愫的根基來源,深植於社會生活中。“悲涼之霧”是托付於“華林”的。
“他所深惡痛絕的,正是他所仰賴的﹔他所反對的,正是他所依靠的”
吳組緗先生意識到俄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某種深刻的類同,尤其是在托爾斯泰和曹雪芹之間。這也啟發了我作進一步思考,我想到曹雪芹與托爾斯泰都出身豪門,都有過荒唐享樂的少年時代﹔他們都用文學來表達自己的深度懺悔與對那些無辜可愛女性的懷念。
在一個深秋,我終於來到莫斯科郊外的托爾斯泰庄園。庄園的住宅建筑不大,房間簡約,空間狹窄。這可能和嚴寒天氣中的保暖有關。在住宅外面是廣闊的樹林和草地,沒有耕種過的生態,給予人一種自由與野性。想象中,女仆瑪絲洛娃與回家來度假的少爺聶赫留朵夫就在這園林裡嬉戲追逐。這其實是托爾斯泰青年時代的放任生活。豆蔻年華的女仆愛上一位青春萌動的少爺,在這座封閉的園林發生了短暫的愛情,女仆付出了畢生的淒慘代價,而少爺回歸他的上流社會。當中年的聶赫留道夫介入一個案件的陪審,發現瑪絲洛娃被誣陷為“殺人犯”,這促使他對貴族社會發生了反省。而那位千方百計要嫁與他的米西,讀來是與薛寶釵的言語風度頗相似的。瑪絲洛娃的出現震動了聶赫留道夫的靈魂。下層人民的真實苦難,以及貴族們的腐敗生活方式,不斷地交織在他的生活中。他決定自己承擔對瑪絲洛娃犯下的不可推卸的罪責。最終他選擇追隨瑪絲洛娃踏上流放之路,托爾斯泰視為靈魂的“復活”。
比《復活》早誕生一個世紀,《紅樓夢》裡也有一位天資聰慧的貴族少爺,同樣被如花的女婢們包圍,也因為孟浪和無心,毀滅過別人的生命。
現在難以確認曹雪芹寫作《紅樓夢》故事的原址。我寧願根據自己游歷過的北京親王府,和蘇杭的著名園林來構想一個大觀園。比起俄國伯爵,中國的貴族住宅奢華得多。亭台樓閣,一件不能少。在這些雕欄畫棟中生活的賈寶玉,也與《復活》中的少爺聶赫留朵夫相類,對府中的女奴也是有罪孽的。
金釧與晴雯都是被王夫人殺死的,起因卻是寶二爺,唯有他明白她們是純潔無辜的,卻又不能援救,所以咒母親為“悍婦”,襲人為“诐奴”。襲人與寶玉間有床笫尋歡的由頭,寶玉卻沒有想過要給她“名分”。襲人的生存發生危機感,為了求得生存與向上爬的空間,她果斷地投靠了王夫人,除掉勁敵晴雯,背棄舊主子賈母。當襲人成為王夫人控制寶玉的心腹,少爺也無法與她爭辯。因為這種女奴也是他私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邪惡由他自己而生。正如柳湘蓮所罵:“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干淨,隻怕連貓兒狗兒都不干淨。”
在一個世紀之后,托爾斯泰寫出了《復活》。在俄羅斯的那個時代,屠格涅夫、赫爾岑等人也寫作過類似的內容,他們都是貴族少爺出身的作家,出於對自己青年時代的荒唐和對這個階層的反思,重新回顧了當時曾經漠視過的女奴的命運,以及自己的罪過。
曹雪芹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感與思想的反省。他放逐了自己的余生,與曾經一體的腐朽之家和傳統決裂了,寫作《紅樓夢》,是為了自己的追悔與那些如花女兒的“復活”。
《紅樓夢》在開篇說:“忽念及當時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並使其泯滅也。”
這裡說到“我之罪”,不可看成是敷衍之詞。而“閨閣”所指,也不只是“小姐”們,在賈寶玉眼中,凡沒有出閣的都是“女兒”。
在往事的回溯中,曹雪芹將自己反省中所得的思考與悲憤,放進了角色,於是賈寶玉的表現就變得矛盾起來,一方面是我行我素、享樂逍遙的少爺,一方面又成了悲天憫人的反抗者和思考者。而這兩方面的本質有著不可調和之處。
吳組緗先生說,“古代作家的世界觀裡頭,尤其是在這種時代轉換的時期的世界觀裡頭,感性認識同理性認識形成尖銳的矛盾。曹雪芹《紅樓夢》就是如此。許多著名的作品都是如此。他矛盾得要命……因此,偉大的作品都是形象大於思維。”“這是可悲的矛盾:他所深惡痛絕的,正是他所仰賴的﹔他所反對的,正是他所依靠的。”
作者描寫了這些弱點的克服,或性格的進一步發展:當林黛玉郁病致死后,賈寶玉並沒有長久和薛寶釵、襲人苟且厮混下去,而是終於拋棄了她們,毅然決然出走了的。
有人說,高鶚續寫的功勞在於他保持了《紅樓夢》悲劇結局。我以為還要再深一步,高鶚寫出一批人“心靈的醒悟”與決裂:黛玉臨終前醒悟,看穿所謂親情的冷漠,她指責寶玉的背叛,燒毀了自己的詩稿。紫鵑、惜春醒悟,以“出家”為決裂。當鴛鴦明白,賈母利用了她,而沒有顧及她此后的生命,上吊了。巧兒甘心嫁入庄戶人家,去過紡線織布的生活。小紅悟得早,跳出賈府,與賈芸另謀生路。襲人以她慣有的“改換門庭、前后不一”之性格,嫁給了伶人,隨機應變也算是一種決裂。
吳組緗先生說,列寧論托爾斯泰時,說他是呆頭呆腦的地主,是不可救藥的基督徒。可是列寧又稱贊他是“偉大的藝術家”“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
曹雪芹是可以與托爾斯泰比肩的中國的文化巨匠,《紅樓夢》無愧“沒落的中國封建社會的一面鏡子”。 (作者:張曼菱,系作家,著有《西南聯大行思錄》《曼菱說紅樓》等)
飛向藍天的“卓瑪”(身邊的小康故事) “卓瑪,飛機能飛多高啊?”“卓瑪你去過哪些城市了?”……每次回家,格茸卓瑪仿佛是村裡的“明星”。 格茸卓瑪的家鄉在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裡拉市小中甸鎮團結村。這個很多人沒有坐過飛機的村子,卻走出了一位在飛機上工作的女孩。 作為東航…【詳細】
雲南新增19例境外輸入確診病例 人民網昆明7月27日電 (符皓)據雲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通報,7月26日0時至24時,雲南無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例19例、無症狀感染者3例。確診病例治愈出院2例(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解除隔離醫學觀察2…【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