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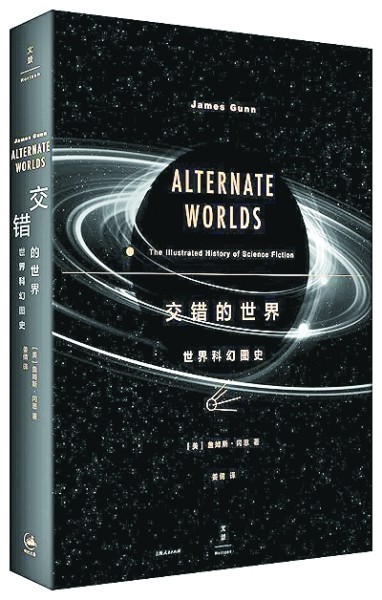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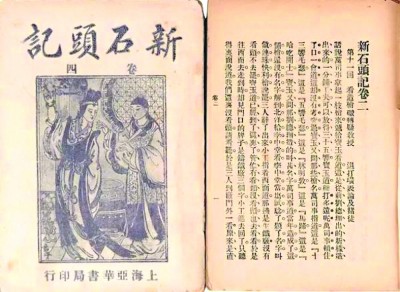

回顾中国科幻的发展历史可见,20世纪初在时代的巨变中,中国科幻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类进步的梦想中汲取了“原力”,并融合了民族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主义精神;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刘慈欣将之发扬光大,写出了中国气派的“星空浪漫主义”,激励我们奋勇前行,也使中国科幻走向世界。在当前,我们所身处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将如何引发科幻艺术的新变?
那种不断向上、追求进步的精神在哪里出现,科幻的种子就会在哪里生长
2020年即将结束之际,全球科幻迷听到了一个悲伤的消息:美国时间12月23日,著名科幻作家、学者詹姆斯·冈恩去世了,享年97岁。冈恩编选的读本《科幻之路》启蒙了无以计数的读者。早在1997年,该书就被译介成中文,成为许多中国读者了解世界科幻的重要指南。他的另一本著作《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则系统地述说了科幻文学的由来与演变。该书初版于1975年,直到2020年才推出中译本。尽管时隔45年,仍然令人激动。
冈恩出生于1923年,比世界上第一份专门性的科幻杂志——雨果·根斯巴克创办的《惊奇故事》还早了3年。他亲历了20世纪美国科幻文化的繁荣昌盛和起伏变迁,对那些重要的作品、杂志、人物都十分熟悉,与不少声名显赫的作家、编辑更是交往深厚,因此能够在讲述历史时如数家珍。另一方面,冈恩从1970年开始在大学讲授科幻课程。《交错的世界》正是以他的讲稿为基础修订完成的,这使得他的叙述在确保学术水准的同时又能做到明白晓畅,与之相比,此前被译介到国内的科幻史类著作多少都带有一点学院派的深奥晦涩。尤其令人感佩的是,以中译本的出版为契机,已经九十岁高龄的冈恩,又在原书的基础上重写了第一章、补写了最后一章,并特别提到了《三体》英文版获奖等近期事件,不但让这本经典科幻史著作在结构上更为完整,也让我们能够透过科幻黄金时代亲历者的双眼去审视近四十年来世界科幻的潮流。这样的视角尤为宝贵,毕竟,与冈恩同代的不少科幻大师早已谢世(为本书第一版撰写了序言的阿西莫夫早在1992年就已故去),可以说,近一个世纪的科幻风景,在冈恩这里被整合成连贯而深厚的生命体验。
在中文版序言中,冈恩开宗明义地指出:“科幻小说是变化的文学,其本身正是变化的最好例证。”围绕“变化”这一核心概念,冈恩生动地描述了科幻的历史:尽管古希腊时就已经有了对理想国的描绘、通过虚构旅行抵达奇异世界的故事,但在漫长的时期里,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态度、战争模式等都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直到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整个世界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加速式的变化,一种新的信念确立了——人类不需要依靠超自然力量,而是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去探索未知,认识宇宙、自然和自我,通过自己的发明创造改变命运,以获得更好的生存能力。在这种信念下,科技发明日新月异,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不但取得了惊人的物质成就,也重塑了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未来”取代了已然失落的“过去”,成为“黄金时代”的新坐标。这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变化,为科幻小说的诞生提供了基础:
也许界定科幻小说的唯一标准是它的态度:科幻小说包含了这样一种基本观念,即宇宙是可知的,而人类的使命就是去了解宇宙,发现宇宙和人类从何而来,如何进化到今天的情形,宇宙和人类又将往何处去,是什么法则在制约它们,最终一切的结局将会怎样,又将如何结束。
换言之,不是先有了一批新颖的故事,世人才懂得了“科学幻想”,而是在一种渴望真理、勇于探索、推陈出新、朝向未来的整体氛围中,科幻小说应时而生,这种因果关系被概括为一句话:“科幻小说理应被视为科幻世界的文学。”正因此,冈恩在勾勒不同阶段的科幻发展时,尤其注重说明当时的科学成就及其社会影响。对于广大科幻迷来说,这是理解科幻的关键入口,正是通过展示现代科技带来的神奇变化和未来的无限可能,科幻为读者提供了最主要的乐趣。这种乐趣被刘慈欣喻为“科幻的原力”,它能够将一切幼稚、粗糙的故事催化成魅力无穷的精神食粮。可以说,冈恩的科幻史,正是一部“原力”的消长史。读完这部历史,读者或许无法记住许多有趣的细节,但一定会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那种不断向上、追求进步的精神在哪里出现,科幻的种子就会在哪里生长。
例如,19世纪层出不穷的新发明,让凡尔纳在欧洲登场。这位法国天才感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召唤,成功地将科技成就变成小说的主题。他笔下那些令人憧憬的新发明,往往以前人已有的技术构想为基础,能够让读者相信未来确实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故事。尽管当时还没有“科学幻想”这个概念,但凡尔纳回应了欧洲人面对科学奇迹时的狂喜,也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成功。到了20世纪,永不满足于现状的科幻精神,在美国这块新殖民地获得了蓬勃的发展。随着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崛起,随着世界各地优秀人才向这里的聚集和大众对通俗读物的需求增长,热衷在科技时代探索未来奇景的出版人顺应时势,通过图书和杂志将有着共同爱好的作者与读者聚集起来,由此促成了科幻的“黄金时代”。冈恩不无骄傲地写道:“科幻小说诞生于法国和英国,却在美国找到了自我。”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发源于英国、在美国得到响应的“新浪潮”运动,开始革新科幻的美学面貌,新一代作家广泛借鉴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技巧,大胆开拓新的题材,包括对人的身体及其他私密领域的探索。在许多人看来,这些作品为了赢得“主流”文化界的认可而牺牲了故事的可读性。冈恩却指出,老派的科幻迷之所以抵制“新浪潮”科幻,根本原因不在于其晦涩艰深的文学技巧,而在于其视角的转变:“新浪潮”作家放弃了此前的科幻文学那种从广袤的时空尺度上审视人类命运、相信理性与科学能够引领我们前进的态度,而将目光重新聚焦于当下的社会和个体的烦恼,并采取了主观主义的、非科学的、“感觉比思考更重要”的视角。不论读者对此抱持何种态度,时代精神确实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让冈恩在初版的结尾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时不无深情地指出,科幻的动人之处在于“一种既高傲又谦卑的哲学”。
可以说,冈恩对数百年科幻史的描述与把握,采用了完全纯正的科幻迷立场,对科幻风尚的变化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所以刘慈欣才称许这本书是“目前国内翻译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科幻的视角写出的科幻文学史”。
在时代的巨变中,中国科幻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类进步的梦想中汲取了“原力”
当然,作为一本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交错的世界》也有其局限:它所涉及的基本上以英美科幻为主体。这或许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但也给今天的中国读者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书中的一段话令人感慨颇深:
到了1840年代,美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人们都已见证了工业革命的考验和胜利,并接受了这样一种社会理念,即科学会带领人类走向崭新的、更加美好的生存状况。
在美国学者笔下,这是闪烁着金色辉光的历史时刻:科技带来的社会变化正在加速,整个世界都为科幻小说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但是,1840这个年份却不可能不召唤起中国人的苦涩记忆。对我们来说,“渴望真理”“勇于探索”“推陈出新”“朝向未来”“理性精神的发展”,只是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的一层面向,而在故事的另一层面,探索未知疆域与殖民者的暴力征服紧密相连。也正是殖民主义为近代中国带来的剧烈“变化”,促成了科幻在中国的生根发芽。
任何文明要持续发展,必然要不断经历自我肯定、自我保存与自我质疑、自我革新的往复,以实现延续与发展的统一。新旧文明的激烈碰撞也会带来文学艺术的重要变化。当西方文明对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变进行肯定与质疑时,科幻的“原力”也激荡成两个方向:对于“进步力”的赞扬(如凡尔纳)和对于“毁灭力”的忧惧(如《弗兰肯斯坦》),两者的交织贯穿了科幻的历史。
同理,中国科幻诞生于本土文明遭遇空前危机的时刻。19世纪,曾经的天朝上国颠倒角色,沦为落后国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西洋文明”中的“进步力”在落后国度面前变成了“毁灭力”,这势不可挡的历史动能向落伍者们抛出了自我保存与自我变革的平衡难题。一方面,否定传统和激进变革的意志由此而来。在这场变革中,以现代科学为基础改造国民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成为重要的文化工作,同时“小说”的功用被拔高,于是“小说界革命”中自然出现了科幻小说的身影。在1902年的《新小说》创刊号上,主编梁启超翻译了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里翁的《世界末日记》,讲述了几百万年后人类文明逐渐凋零的故事。结合梁氏当时的宗教思想,可知他翻译这篇科幻小说的目的是要展示天文学尺度上的末日图景,让国人能够改变好生恶死的心态,放下对红尘的贪恋,变得勇猛、刚毅,投身到舍生取义的大无畏事业之中,为拯救苍生而献身,肉身虽会陨灭,地球虽会灭亡,但灵魂和爱会在星空中永生。这种看法,呼应了以身殉道的好友谭嗣同,在后者看来,人与人、人与万物的隔膜造成了世间的不幸,通过“以太”这个物理学家假定的无所不在、遍布宇宙的介质,个人的至诚就能够感动他人,冲破彼此的隔膜。英勇就义之时,他一定在期许自己的死亡可以激起更多人的热血。他甚至还曾设想,既然人类进化不止,总有一天会摆脱肉体的束缚,变成纯精神性的存在,在宇宙中遨游。换言之,正是现代科学促成的三观革命,赋予仁人志士舍生取义的勇气。
另一方面,这种英雄气概又和一种国际主义精神融合在一起:先觉者们不仅要挽救自己的民族,更要为人类的和平共存谋划出路。24岁的梁启超曾这样表白:“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这意味着,不但要以西方文明为鉴革新自我,也以自我的困境为切入点去思考西方文明的弊端,在东西互鉴中为人类文明寻求新的价值与方向。正因此,中国科幻从一开始就深受西方科幻的影响与启发,同时也在模仿与改写的尝试中探索自己的道路。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被梁启超改造成了闻名后世的“睡狮”,饱含“毁灭力”的文学形象竟演变为富于“进步力”的民族寓言,实属阴差阳错(学界早有考证)。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则让贾宝玉重生在20世纪初的中国,历尽社会黑暗之后进入科技发达、道德至善的“文明境地”,其中乘坐飞车、驾驶潜艇的部分明显模仿、戏谑了凡尔纳的故事,全景式的乌托邦描写也有着爱德华·贝拉米《百年一觉》的影子,但作者的意图绝不在于拙劣的模仿,而是要通过科幻小说这一新的文学方法,探讨一个“真文明”世界应有的技术与道德水准,以此映衬和揭露列强在“文明”的假面背后恃强凌弱的本质。对此,曾翻译过凡尔纳的青年鲁迅也深有感触,后来的他虽然不再热衷科幻小说,但在《破恶声论》中对“黄祸论”的看法,也与同时代中国科幻小说里不时出现的黄种人大败白种人的复仇幻想构成了对比:如果未来中国能够强大起来,不应重走列强的老路,而应去扶助弱小,使他们摆脱奴役、获得自由。
简言之,近代中国虽然饱受欺凌,但在顽强的求生意志下,产生了奋发图强的精神和英雄主义气质,这种精神和气质又受到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的激励,化作对美好未来的信念和为信念牺牲的勇气。20世纪初的中国科幻也正是在时代的巨变中,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类进步的梦想中汲取了“原力”。当然,科幻文艺的繁荣终究要以综合国力作为坚实基础,法、英、美、苏、日等国的科幻发展中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直到20世纪末,才出现了通过《鲸歌》登上历史舞台的刘慈欣。2006年,《三体》开始连载。2010年,《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出版,开始在科幻圈外引发轰动。从1999年到2010年,这是刘慈欣个人成长的阶段,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直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阶段,是中国高校开始扩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基数逐年增长的阶段,也是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并最终在2011年首次实现城镇人口比重过半的阶段。正是这样的历史变化为中国科幻的蓄力提供了能量,为《三体》的成功奠定了文化土壤和群众基础。在“变化”与“原力”的视角下,我们能够发现刘慈欣的故事里蕴藏着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苦闷与追求,它们挑动着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焦灼与渴望。
首先是强烈的进化压力与生存焦虑。多年来,这位长期居住在山西娘子关的工程师小说家一再表达对于科学探索尤其是基础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期待,对于人类不能永远停留在地球而必须进入太空以获得更广阔生存空间的信念,对于在极端条件下为保全整个文明而必须采取诸多反道德直觉之举的拥护。在《乡村教师》里,罹患绝症的老师在临终之际仍在要求懵懂的孩子们背下他们不能理解的牛顿力学三大定律,出人意料的是,神一般的外星文明在清扫战场时鉴定着沿途行星的文明等级,被随机抽作地球样本的孩子们面对一系列测试题时无动于衷,直到正确答出了牛顿定律,才证明了地球值得保存。以奇异的方式,作家再次道出了文明降级后失去生存资格这一久远的忧虑。有趣的是,早在一百多年前商务印书馆翻译的凡尔纳小说《环游月球》中,就已提到日、地、月的运动属于“三体问题”。在原著的另一个译本《月界旅行》中,译者周树人在序言里曾推测人类如果能够殖民外星,恐怕“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从鲁迅到刘慈欣,对生存与灭亡的思考始终位于百年中国科幻的核心。
其次是通过超感官冲击促成三观改造,完成文化的革新。年轻时第一次读完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后,刘慈欣感到一种“对宇宙的宏大神秘的深深的敬畏感”。在他看来,科学描绘的宇宙图景远比科幻小说震撼,科幻作家只是通过小说把这种震撼“翻译”出来,传递给读者。在随笔中,他说希望通过科幻让忙忙碌碌的众生能停下匆忙的脚步,仰望星空,感受宇宙的浩渺。在小说中,他试图用现代汉语展示宇观尺度的事件,让我们有限的个体经验和喜怒哀愁在超感官的冲击中得到洗礼。在最极端的《朝闻道》中,科学家甚至愿意以生命为代价,换取认识科学真理的十分钟。在历史的参照系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经常描写地球末日、太阳系末日乃至宇宙末日的当代作家,和20世纪初翻译《世界末日记》的梁启超一样,也试图通过文学的工作来推动民族精神的更生。
不过,尽管刘慈欣的故事看起来很黑暗,人类在宇宙面前看来微不足道,但又因为能够认识到“真理”而伟大,因进取而崇高,因失败而悲壮。这种悲壮,正是人类生存意志和种族尊严的表达,因此营造了一种英雄主义气氛。这在《流浪地球》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太阳系演变为红巨星的灾难,本应几十亿年之后才发生,小说家却让其极速降临,于是在危机和解决危机的手段之间造成了极大的不匹配:人类在地下世界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只为能够驱动地球离开太阳系,以如此笨拙的方式来逃亡。茫茫冰雪覆盖的地表上,巨大的工业体系艰难维持运转,标示着人类的国际合作精神与顽强抗争意志。
总之,刘慈欣小说对生存的焦虑、对进化的执着、对科学的崇拜以及对人类团结合作谋求文明延续的憧憬,正是近现代中国核心命题在星际尺度上的再表达。
刘慈欣把民族的英雄风骨投射到未来的时空里,写出了中国气派的“星空浪漫主义”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了不起的人物,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通过历史记载和文学艺术的演义,成为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塑造了人们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和情感。比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壮士悲歌;比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盛唐气象中的文人风骨;比如义薄云天、不畏豪强的关云长,是普通人对于忠义的寄托;比如“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是为了保卫家乡而不惜流血牺牲的勇气,是为了建设家乡而改天换地的气魄,也是敞开家门迎接四方来宾的气度,更是对世界和平的美好期待。所有这些故事浇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培育着民族自豪感,在困难的时代激励我们奋勇前行。刘慈欣小说的魅力之一,就在于把这样一种英雄风骨投射到了未来的时空里。
如果说,在20世纪的中国大众文艺谱系里,金庸塑造了一系列古代中国的英雄,是一种“历史浪漫主义”,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塑造了一系列现代中国的英雄,是一种“革命浪漫主义”,那么刘慈欣就是塑造了一系列未来中国的英雄,是一种“星空浪漫主义”。有一段时期,好莱坞电影让我们习惯了美利坚的黑白英雄拯救世界的叙述,直到《三体》的出现。通过恢弘的设定、庞大的骨架、复杂的情节,刘慈欣摹画了一组未来人物群像,其中有史强这样强悍粗鲁、狡黠命硬的警察,有章北海这样冷酷果决、缜密隐忍的太空军政委,也有触发危机的叶文洁和力挽狂澜的罗辑。这些人物在命运攸关之际的抉择,让读者津津乐道、争论不已,像谈论赤壁之战一样谈论地球的太空舰队如何被三体人的“水滴”探测器轻易摧毁,像谈论荆轲刺秦一样谈论章北海为了扭转未来太空军的发展方向如何精心策划太空暗杀,像谈论萧峰为了宋辽息兵而自尽于雁门关外一样谈论罗辑如何在荒郊独自向三体人喊话并以自杀威胁迫使对方放弃侵略以免两个物种同归于尽。正如金庸的成功不仅是因为他熟谙传统文化,更因为他写出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刘慈欣的成功也不仅在于他奇异而宏大的技术想象,更因为他写出了中国气派的星空浪漫主义,通过激动人心的虚构时刻,将我们对古代、现代和未来的中国英雄的想象勾连在了一起。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与全民科学素养的提升,同时也由于科技的发展使得不少过去的科幻场景正在变成现实,今天的人民大众对科技话题的兴趣日益浓厚,对太空时代的人类命运也更加关心,刘慈欣为这样的读者讲述了古老农耕民族的觉醒和新生,谱写了人类在太空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当然,这绝不是说,刘慈欣的作品是完美的。相反,如果以最高的艺术标准来衡量,他的小说有着显而易见的不足。这很正常。在由远古的神话、庄子的寓言、屈原的赋、李白的诗、东坡的词等所构建的华夏文学长河中,伟大而浪漫的心灵虽然一次次奏响过生命的律动,创造了众多不朽的篇章,但如何用现代汉语去表现科学革命之后的时空之广袤、探索之艰辛、定律之奥妙、技术之恢弘,抒发现代中国人的豪迈和悲悯,则是一个多世纪前才出现的全新任务。刘慈欣的作品,只是中国作家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探索之后取得的阶段性成绩,有其里程碑式的意义,但也映衬出中国科幻整体实力的相对单薄。
在当下,还需要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所身处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如何引发科幻艺术的新变?在科幻与现实的对照下,中国的科学幻想,该如何理解自己的当下处境,思考未来的出路?下一个能够切中时代脉搏、道出人们内心深处的忧患与憧憬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子?当开阔的胸怀、进取的豪迈、大无畏的勇气、为追求真理和为人类福祉而奉献的决心等曾经推动科幻走向辉煌的核心精神在全球诸多角落呈现凋萎之态时,我们是否还能充分汲取现代文明成就中的“原力”,实现民族精神的茁壮成长,进而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愿我们勉力前行,并用冈恩的这段话不断提醒自己:
科幻小说就像是来自未来的书信,写信人是我们的后代,敦促我们小心保护他们的世界。 (作者:飞氘,系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飞向蓝天的“卓玛”(身边的小康故事) “卓玛,飞机能飞多高啊?”“卓玛你去过哪些城市了?”……每次回家,格茸卓玛仿佛是村里的“明星”。 格茸卓玛的家乡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团结村。这个很多人没有坐过飞机的村子,却走出了一位在飞机上工作的女孩。 作为东航…【详细】
云南新增1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人民网昆明7月27日电 (符皓)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7月26日0时至24时,云南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9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2…【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