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牢山三夜:一篇篇幅是見報稿兩倍的採訪手記
編者按:
先是一個生態版頭條報道西黑冠長臂猿種群監測,后是記者調查一個整版報道綠孔雀保護,6月9日、10日,人民日報接連大篇幅報道雲南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而報道區域均是位於滇中的哀牢山。作為首位進入哀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核心區的記者,任憑思緒飛揚寫下了這篇哀牢山三夜。
記者曾在魯甸地震當晚趕到震中龍頭山,也曾跟隨護航編隊報道湄公河巡航、夜宿金三角﹔但此行深入哀牢山核心區,是入滇十年來最難的採訪。作為記者手記,篇幅很長,以致超過了見報稿兩倍。但正如文末所言:這是記者一次難得的採訪,卻是護林員的日常。僅以此文,向一線動物保護工作者致敬!
預報未來三天無大雨,記者3月21日星夜趕赴雲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縣者竜鄉,以便次日跟隨哀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新平管護局巡護員進山,體驗式採訪西黑冠長臂猿種群數量調查。
對外,記者說去玉溪報道西黑冠長臂猿,卻沒敢報告是進哀牢山。山中天氣瞬息萬變,去年曾有4名地質調查隊員在哀牢山遇險﹔出發當天發生空難,上山之后手機信號中斷,不管是否真的存在危險,擔心總歸難免。
但西黑冠長臂猿,就在那哀牢山裡。作為記者,很難抵抗首次挺進自然保護區核心區的誘惑,何況還有望聽到西黑冠長臂猿美妙的“二重唱”。
一路平安,但並不順利。
【馬鹿場匯合】
此前,因為採訪綠孔雀,記者見到了哀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新平管護局局長郭斌,他看記者身板還行,盛邀記者進山採訪西黑冠長臂猿種群監測。國內長臂猿物種數量不少,但從個體數量上說,八九成是西黑冠長臂猿。
機會難得,記者卻沒敢立馬答應:長期報道生物多樣性,記者並不怕負重一二十斤、走五六個小時山路的辛苦,也充分相信當地調查隊員的專業性,但誰也沒法完全忽視進山的危險性——那天下山時,遠處晚霞映紅了天,新平管護局者竜管護站馬鹿場哨所外卻突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沒有手機信號的核心區如果遇到這樣的天氣,對安全將構成極大的威脅。
郭斌局長答應安排李林國跟記者同行,堅定了記者進山的決心。五年前,記者曾在哀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試驗區茶馬古道附近採訪過外號“林子”的李林國,他家就在者竜鄉,小時候經常一個人進保護區核心區。路熟,可提高安全系數﹔追猿七八年,他在樹下唱歌,“習慣化”的西黑冠長臂猿一家在樹上該干嘛干嘛,李林國是西黑冠長臂猿的“土專家”,一路都可採訪。

核心區巡護
此次進山,機會窗口很短。西黑冠長臂猿種群數量調查為期一個半月,但今年雲南三月下雨的天數比往年要多。一旦進入雨季,山路難行尚且可以克服,山路濕滑將導致受傷的風險大增﹔特別是在核心區內,避雨、取暖會出現巨大的困難,受傷、生病卻不能及時從山中撤離,一旦失溫,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上午接到通知,中午處理完手頭工作后,記者就從昆明直奔新平,趕到縣城時已是晚上六點。簡單吃過晚餐、取上裝備,抵達者竜鄉管護站時,已是晚上九點半。此次新平縣西黑冠長臂猿種群數量調查,共分者竜、水塘和嘎洒三個片區,者竜離縣城最遠,但西黑冠長臂猿也最集中。
早上10點,記者跟護林員陸續前往者竜管護站集合。見到李林國,記者懸著的心,落定了大半。分社司機、此前當過兵的楊艷波也堅持上山:“與其在山下干著急,還不如上山陪著你。”
加上本地護林員鐘應興鐘叔、張貴昌張叔和李忠華、李富勇兩位80后,一行七人計劃在22日中午抵達保護區核心區外圍的馬鹿場哨所吃午飯,然后耗時四個小時抵達宿營地﹔夜宿營地后,23日一早7:00前趕到附近的聽點開展為期半天的西黑冠長臂猿種群數量調查﹔下午拔營前往白沙河營地﹔24日,上午在白沙河參加完調查后,保護區同志將接應記者下山,而林子一行繼續開展為期三天的調查——由於西黑冠長臂猿並非每天鳴叫,為了避免遺漏,每個聽點都需要連續三天的監測。

護林員在哀牢山國家自然保護區巡護
為了減輕負重,記者不僅沒帶電腦,連採訪本多余的紙張記者都拆了下來。野外工作忌諱逞能,不給監測隊員添麻煩,算是記者此行最大的貢獻。
除了睡袋、雨衣、膠鞋、迷彩服、防潮墊這樣的裝備,此行最大的負重是食品和藥品。食品最主要的是肉、米、面條﹔上山一次其實對於巡護人員來說也同樣不容易:最基本的便是帶上充足的食物。藥品除了白藥還有蛇藥——盡管雨季尚未來臨,但山中不比鎮上,一旦用到卻沒有,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不過對於年近六十的鐘叔來說,他還有自己的必需品:10斤白酒。十幾年的護林員生活,為了驅寒,鐘叔有些酒精依賴,飯后睡前必飲酒,且是用海碗豪飲。
除了常規負重,五位監測人員人手一個打火機,還分別帶了鬆明子、蠟燭、薄輪胎。記者后來才體會到,如果不是長時間在山裡,保暖遠比食物重要。
【挺進核心區】
想到進山難,沒想到進核心區會那麼難。
從者竜管護站到馬鹿場哨所,有條土路,開車一個多小時。在馬鹿場哨所吃過午飯,林子提醒記者將水壺灌滿﹔上山前,同齡的李忠華遞給記者一根木棍,記者開始隻當“悟空有了金箍棒”﹔上山后才明白,登山棍一樣是進山必備裝備——無樹的陡坡,幫助記者爬上去﹔河畔陡崖,防止落水或者滾下山去。

國家一級保護植物水青樹
下午一點多,調查隊員正式從馬鹿場哨所出發。林子很快走在了前面,但又很快放慢了腳步——他怕記者吃不消,故意壓慢了速度。
“你們上山就像我們進城,肯定不習慣。”五年前採訪林子,我們聊的都是西黑冠長臂猿,五年沉澱,我們彼此的了解更多停留在朋友圈。但人生有幾個五年?再次相見,感情無需多言。
林子告訴記者,除了保護區工作人員和極個別專家,哀牢山保護區核心區極少有外人進入,記者將是進入新平縣內哀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核心區的第一個媒體人。
因為走得不快,記者採訪的習慣很快暴露,不停跟林子提問,林子有問必答。持續上坡,腳踝生疼。記者問走了五分之一沒,林子說沒有,記者說六分之一有了麼?林子看了眼時間,說:“我們走了半小時,而到目的地需要四個多小時。”他說:“你別管多遠、也別管多難,你一直走,就到了。”
四五十度的上坡是累,七八十度的坡度是難,向下的斜坡則是險。山路難行,好在登山棍給力。最近一年,記者每周三次兩公裡沉澱的體力和引體向上手上磨出來的老繭幫了大忙——杵棍子時,掌心的老繭磨開了口子,虎口生疼。而記者只是單純背著自己的裝備,林子每人卻還需要備著十幾斤肉、菜、米。對於鐘叔這樣的護林員來說,每月他們至少要在自己的轄區巡護22天,每月要集中巡護一次。

保護區內的雲南鐵杉林 刀元忠攝
即便是在林中,人依然是王者。一路上,野豬、熊的痕跡到處可見﹔鼯鼠、麂子的叫聲若隱若現﹔記者沒有目擊獸類,倒是鳥時不時穿越林間。
這倒不是因為林中野獸少。“哪有動物不怕人?”張叔說,視力、聽力、嗅覺,野獸都比人好得多,早早發現人類靠近就會遠遠回避。反而是森林中的蛇和螞蟥,對巡護人員來說更危險。
為了確保我的安全,哪怕記者走再慢,李忠華也會跟在記者身后。既避免前方遇到危險,也避免記者跟不上隊伍落單。時不時飄來的大霧,彌漫茂密叢林,十米外就會見不到人,一旦山中迷路,會有生命危險。
一路上時雨時晴,林子表情也越來越嚴肅:一旦下雨,此行將充滿變數。隔一段路程,林子會讓大家歇腳。林子選的歇腳點,既可以補水,也能跟外界聯系。“護林員巡山時收到短信,才發現有些山頭有手機信號。”
歇第三次后,記者跟隨林子繼續上路,體能已快耗盡。可能是看記者越來越吃力,極少言語的李富勇喊了句:“還半小時就到啦!”像是自言自語,但用的卻是普通話。
下午五點,遠遠看到一個白色防水布搭建的棚子——原來李富勇真沒騙人。沒有半點興奮,記者一下子癱坐在地上。脫下濕透的衣服,發現后背已經滿是鹽漬繪制的地圖。

林子他們卻沒一個人閑著:鋪防潮墊、取柴、生火、做飯。不多久,記者就看到了外面冒起的炊煙。“雨不大,火好生。”李忠華跟記者比劃:最好用的是衛生紙,上面把木頭搭成三角架,下面放枯葉,然后用衛生紙點,不難﹔不過李忠華也說,雨季最好少在山上過夜,晚上冷得很。
這時記者才有精力仔細端詳營地:一個坡度相對較小的背風坡,幾根木頭搭建頂,覆蓋一層塑料防水布,便是當晚的夜宿點﹔坡下是條小溪,取水方便﹔加上旱季,臨走時好熄滅火堆。

鐘叔很快將五花肉串起來放在火堆旁煙熏,一來減輕重量,二來防止變質。李忠華用木頭削尖給記者串了幾片肉,示意記者烤著吃。“上山吃的管夠。”李忠華告訴記者,菜會選擇容易保存的,而肉會根據天數確定帶多少,米則會有余量﹔最初肉新鮮,適合煮或者烤﹔之后肉會炒、炸。在山裡才發現,最原生態的吃法是燒和烤﹔煮、炒、炸反而需要器具。
晚上六點,我們圍坐在營地前面的桌子上吃飯——桌子其實是塊木頭,用砍刀砍平﹔座位則是原木。這時記者才發現,李忠華粗中有細:在他手裡,砍刀不僅用來開路、砍枯木,剁肉、切菜,甚至還可以做桌子、削筷子。

當晚,記者沒有洗漱。到了野外,干淨衛生跟人已經無緣,最大的需求是生存和安全。
【營地侃猿】
當晚,記者依然被林子他們擠在最中間,避免著涼。怕半夜冷,記者將烘干的衣服全部穿上,早早鑽進了睡袋。
核心區第一夜,記者睡得並不好。半夜下起了淅淅瀝瀝的小雨,雖然防雨布並沒有漏水,可是七個人呼出的水汽凝結在防水布上,外面雨一沖擊,小水珠再次打散成水霧,落在臉上。時不時被冰醒,記者索性將臉埋進了睡袋。后半夜睡熟,一睜眼已經是七點。
林子說,當天下雨,上山開展西黑冠長臂猿種群調查的計劃取消。其實聽點不遠,離營地也就半小時。“下雨它們也不經常叫。”林子說,下雨天冷,西黑冠長臂猿的活動頻次下降,考慮路上安全,加上覺得次日還有機會繼續聽猿,林子決定在營地靜觀其變。
走出帳篷看天氣,記者感覺有點鼻塞。林子找出感冒藥,李富勇則從火堆裡翻出燒透的木炭,扔進干茶裡,澆上熱水自制涼茶,兩大碗灌進去,記者身體才暖和過來。

吃過早飯,索性在營地跟林子侃猿。其實這次來者竜片區開展種群調查,林子是臨時抽調。他自己的轄區,在哀牢山保護區的試驗區茶馬古道。此前,他和另外兩位同事實現了對西黑冠長臂猿“小新”一家的“習慣化”。
為了知道西黑冠長臂猿家庭結構、關系如何,2010年,林子和另外兩位同事開始在專家指導下開展西黑冠長臂猿“習慣化”觀測——通俗說,就是靠近西黑冠長臂猿所在的樹,近距離觀察西黑冠長臂猿的行為。
生活在樹冠層的西黑冠長臂猿,其實想要見一面特別不容易,保護區有的工作人員二十多年隻見過一次西黑冠長臂猿。“但大家都知道哪裡有西黑冠長臂猿,它們獨特的叫聲,可以傳到兩公裡外。雄猿領唱,然后雌猿跟唱,幼猿會附和兩句。通過叫聲,能夠大概判斷這個西黑冠長臂猿家庭的構成。”林子說。
西黑冠長臂猿生性警覺,別說見到人,稍微聽到一點動靜就遠遠跑開了。林子知道追猿不易,但毅然參與了“習慣化”監測。他說:“局裡出錢,認識我們自己家鄉的猿,沒有理由不參加。”

“習慣化”監測依然是從尋找猿啼開始。有時幾天才能聽到一次叫聲,最多一次40多天沒有聽到西黑冠長臂猿叫聲,林子還以為“小新”一家搬走了。
為了追猿,林子和同事四點就要起床,5點不到就要吃完飯。六點前到山頂,然后根據猿啼去找猿、追猿。晚上回到觀測站往往已經九點,晚飯都不想吃了。林子和“小新”一家的第一次見面,隻持續了兩分鐘。林子興奮的第一時間找到有手機信號的地方,向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蔣學龍報告:“終於見到了!”第一年,見了十幾次,累計碰面隻有一兩個小時。花了近兩年時間,許是西黑冠長臂猿累了、懶得再躲,也可能是西黑冠長臂猿確信林子不會傷害它們,才終於實現了對西黑冠長臂猿家庭“小新”一家的“習慣化”。
林子說,2011年,“小新”一家領地內,出現一大一小兩隻母猿,看體色像是姐妹倆。他給兩群分別命名為A群和B群。很快林子便發現,“小新”頻繁在兩家西黑冠長臂猿間穿梭﹔而A群的女主人則展現出強勢的一面,時不時來驅趕B群成年雌猿。

雌性長臂猿
一開始,小新會照顧兩群猿,2013年初,B群的成年雌猿生下“小新平”,“小新”干脆留在了B群。被激怒的A群女主人,時不時跑來驅趕。哪怕是林子他們在林下通過呼喊勸架,也全然不顧。
隨著“小新平”慢慢長大,B群雌猿開始教“小新平”學著獨立生活:三個月大,雌猿開始用腳拉著“小新平”倒立,讓它逐漸習慣樹上生活﹔之后,讓“小新平”嘗試抓著樹干,時不時用腳拉下“小新平”看它是否能夠抓牢﹔“先是樹枝濃密之處,慢慢才去稀疏的地方,就像咱們教孩子走路。”林子說這話時,仿佛在說自己的孩子。
實際上,“小新”一家可能也將林子他們當成了朋友。林子說,有回他正在監測,突然發現“小新”一家迅速來到了他的頭頂,隻聽身后樹葉刷刷作響,才發現是群灰葉猴前來挑舋,看到護林員,灰葉猴不敢上前,隻能示威后離開。“‘小新’相信我們會保護它們呢!”林子說。

長期近距離觀察,林子能從猿啼中分辨出喜怒哀樂。一般而言,才組建的家庭往往在一年后才能實現優美的二重唱﹔而孤猿的鳴叫中又往往帶著幾分哀怨。有回A群雌猿捉到一隻鬆鼠,小新湊近想要分享,沒想到搶的時候鬆鼠掉到了地上,惹怒了雌猿。“那幾天,‘小新’叫的時候雌猿不叫﹔雌猿叫的時候‘小新’也懶得理。‘小新’一靠近雌猿,雌猿扭頭就離開。”林子說,夫妻感情好的時候他們也會擁抱、親吻,有次“小新”生病差點從樹上翻下去,雌猿一把拽住﹔下雨的時候,“小新”又會和雌猿將“小新平”夾在懷裡。
林子說,這幾年,“小新”越來越懶得動彈,有時候干脆躺平隨便林子觀察。而“小新”的原配這幾年也再未生育小猿。林子猜測,“小新”夫婦可能已經上了年紀,體力不比從前。“我說的這些是我看到的,要是想了解西黑冠長臂猿的習性,還得問蔣學龍老師。”

【聽點聽猿】
3月23日,雨時斷時續,沒有半點要停的意思。睡前商量,24日如果雨停了,拔營前往下一處營地白沙河﹔如果依然大雨,我們則原路返回。看出記者失落,林子安慰:“不管怎樣,我都帶你去聽點聽猿!”
擔心第二天生火困難,當晚沒有澆滅篝火。夜裡四點,記者被大雨聲驚醒,聽到鐘叔起夜出去重新添柴。前半夜狂風大作,后半夜大珠小珠落玉盤﹔第二天一早,李忠華早早起床繼續添柴,只是這次他沒有撿拾地上的樹枝,而找了些長在樹上的枝杈。李忠華說:“地上的枯枝如同海綿,含水量更高,反而更難引燃。”山中生活,經驗是可貴的財富。
7點整,林子如約帶記者到楊吉利山聽點。張叔、李富勇沒二話,又一前一后陪著上山。因為此前已完成了楊吉利山的三天調查,沒有硬性工作任務的林子一路上格外輕鬆。
其實,想見到西黑冠長臂猿並不容易。有保護區工作人員參加工作20年,隻見過一次西黑冠長臂猿。此行記者的目的也並非見西黑冠長臂猿,而是聽猿。

猿啼有兩個作用,一是呼喚家庭成員聚攏——晚上可能不同西黑冠長臂猿會棲息在不同樹上,相當於集合號﹔二是宣示領地,“我家叫的響,你敢過來試試”,大概像示威口號。此外,有些才成年的西黑冠長臂猿,會通過鳴叫尋找異性,求偶組建新的家庭。
西黑冠長臂猿有很強的領地意識,一群西黑冠長臂猿的活動半徑大概為500—1000米的山林。如果沒有山梁阻礙,猿啼能傳到兩公裡﹔每支調查隊伍會分做兩組,在兩個聽點同時記錄猿啼的方位和聲音大小,通過三角定位就能大概確定猿群的位置。五百米內的猿群,除非同時啼叫,原則上算作一群,從而數出西黑冠長臂猿的群數。為了避免西黑冠長臂猿偶爾不叫,每個聽點至少要連著聽三天。如果有的片區有近期的猿群目擊記錄但是沒有聽到猿啼,則再去補聽。
聽點選擇很有講究:最好選擇眼前開闊的山梁,那樣可以聽到四周的叫聲,不容易被阻礙﹔數量太多,工作量太大,難以在雨季來臨前完成種群調查﹔聽點太少,又很可能出現統計遺漏,導致種群數量偏低。有了上次的經驗,這次40個聽點比上回的187個聽點大大壓縮。

護林員在雨中聽辨西黑冠長臂猿叫聲
不到七點半,記者一行冒雨抵達聽點。雨時大時小、時下時停,加上山頂風大,汗水雨水被風一吹,凍得記者直哆嗦。林子說,以前寒冬臘月陪專家上山聽猿,為了驅寒,有的專家喜歡搖樹,有的專家則靠跳躍,有回說著說著,隻聽“哎呦”一聲專家不小心摔下了溝裡。
半個多小時,依然沒有聽到猿啼。林子說:“再等等,我覺得你是有緣人。”閑聊間,一聲猿啼隱約傳來,林子和李富勇立馬進入狀態,開始記錄時間。先是雄猿領唱,后是雌猿合唱,遠遠地傳到聽點。猿群很給面子,足足唱了8分鐘。
林子迅速確定猿啼的方位和距離,給記者示范如何在圖上打點。借著打點的機會,林子比照此前記錄,告訴記者這群猿此前已經聽到過。記者心滿意足之際,又有一隻猿連續叫了兩聲。“這是雌猿,此前也有過記錄。”林子告訴記者,楊吉利山這個聽點覆蓋范圍內,第一次調查有5群西黑冠長臂猿,今年這次調查至少聽到了8群。

護林員用手機辨別長臂猿叫聲的方向
林子坦言,西黑冠長臂猿的種群數量調查,採取的其實是統計加估計的方式。一方面,需要調查人員在聽點統計西黑冠長臂猿家庭群數量,基本准確的統計出一個片區有多少群西黑冠長臂猿﹔另一方面,每群大概有多少隻西黑冠長臂猿個體,則通過訪談結合計數等確定一個系數,乘以猿群數便是西黑冠長臂猿的數量。這也是為什麼不少西黑冠長臂猿種群數量採取“多少群、多少隻”表述的緣由。
9點左右,看記者冷得很,林子提議下撤。林子介紹,如果是正式調研,需要從7:30聽到11:30,但絕大多數時候都是漫長的等待。
這並不是一次完美的調查過程。但林子說:“種群數量調查,本來就沒法保証每次都成功。”
從聽點回到營地路上,林子專門上山找到有信號的地方跟者竜保護站站長李忠文聯系,確認未來仍然有雨,再繼續到白沙河監測很難找到不潮濕的地方搭建營地,林子決定放棄原本的監測計劃,拔營回馬鹿場哨所。
“其實山裡不怕雨,怕的是冷。如果是冬天,這樣的雨一下我們立馬就要下山,否則一旦大雪封山,會有生命危險。”林子說,哪怕是下再大的雨,護林員也都能生起火來,但是連續幾天下雨,地上太潮濕,晚上扎營睡覺是個大麻煩。

【暫別哀牢山】
回營地吃過早飯,鐘叔將碗中的一兩白酒一飲而盡,我們開始后撤。此時,鐘叔帶來的十斤白酒已經剩下不到一半,倒是大米沒吃多少。記者發現,幾位護林員之間很少聊天。林子解釋,這倒不是彼此之間沒有共同語言,長時間在一起,護林員之間該說的早就說完了。
下山大多數是下坡,林子心情不錯,說:“在野外,爬坡你別叫苦,下坡你也不用覺得幸福。你爬的所有上坡,回程都是下坡。”
“其實巡山護林習慣了還好,你是趕上了下雨,平時不咋個。”李富勇說,這幾年同齡人多半已經外出務工。“我們上山巡護是保護,他們進城務工、少打擾這片林子,其實也是保護。”其實,護林員的收入並非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對李富勇來說,護林員的兩萬多元收入,夠一家人日常花銷,加上不影響農活,又能就近照顧家人,他覺得是份不錯的工作。
“要想賺錢,還是要出去務工。”鐘叔家裡種了橙子、沃柑、血橙,一年收入十幾萬。“我就愛大山裡這口空氣。”林子調侃:“也舍不得我姐!”對大多數護林員來說,與其說是為了巡山護猿,不如說是為了給家人更多陪伴。
除了護林員的工資,林子加工茶葉一年有兩萬多的收入,家裡並不寬裕。“錢多買東西就挑一挑,錢少就省著點花。但我得趕在孩子讀大學前,給倆孩子一人攢十萬塊錢。”林子說。林子家離茶馬古道開車要一個多小時,為了省錢,他一兩周才回一趟家。前不久,林子咬牙花9000元錢買了輛二手車,他說:“騎摩托車,膝蓋冷的受不了。”
“這趟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咱們7個平平安安。”下山路上,張叔話多了起來。常在山裡走,哪怕最優秀的護林員也難免受傷。去年林子滑倒恰好被自己的刀劃傷,手指縫了五針。
記者在不少大樹下,看到成千上萬顆種子。然而,絕大多數可能只是鼠類的食物﹔而幸運沒被吃掉的,可能也未必能夠落到泥土上﹔即便發芽,也未必能夠躲過有蹄類動物的啃食﹔長成幼樹也不是萬事大吉,無法跟父輩爭搶陽光,可能也會慢慢枯死。“生命是場意外的驚喜。”林子說,大樹的死亡,可能給幼樹提供生存空間。一趟哀牢山,讓記者重新認識了大自然。
開路的鐘叔,時不時刷一下竹子、鋪墊下石頭﹔拖后的李忠華,則時不時拖幾根木頭搭橋。過段時間,他們還要繼續上山調查西黑冠長臂猿種群數量。

返回馬鹿場哨所,已是中午。記者脫下鞋子烘烤,才發現褲腿上沾滿了血污,才發現被螞蟥偷襲。兩日大雨,車無法開上馬鹿場哨所,記者一行隻能步行下山,直到五點才抵達山下最近的村子。
李忠文早已煮好姜湯准備。腳底生疼,大家歇腳,話題也自然回到了西黑冠長臂猿保護。“雖然還在調查過程中,但從目前已調查區域的數據看,新平縣內的西黑冠長臂猿種群數量明顯增加了。”李忠文說,西黑冠長臂猿是這片樹林的傘護物種,種群數量的增加也意味著森林質量的改善。
“哪怕是保護區外圍的林地,現在人為干擾也很少。”李忠文說,隨著電替代柴,農戶已經很少上山﹔保護區內,重樓居群也逐漸開始恢復。

根據記錄,西黑冠長臂猿在野外的壽命也就是二三十年。8、9歲西黑冠長臂猿才會性成熟,懷孕七個月,哺乳期兩年半,正常生育間隔會在三年以上,一隻雌性西黑冠長臂猿一生也就是三到四胎。由於西黑冠長臂猿家庭是一夫一妻或者一夫兩妻的家庭式生活,一旦附近沒異性,就會出現孤猿,棲息地碎片化對西黑冠長臂猿種群繁衍的影響格外大。
林子說,西黑冠長臂猿繁殖周期長,保護想要明顯見效得花上幾十年。“茶馬古道那片其實是次生林。隻要開始保護,什麼時候不嫌晚。“林子盼望“小新平”是隻雄猿,那樣或許可以接班“小新”,成為新的家長。
李忠文表示,除了棲息地保護、生態廊道修復,科學有效的監測、對西黑冠長臂猿習性的研究同樣重要。此前,林子曾經嘗試用紅外相機拍攝西黑冠長臂猿活動,然而生性警惕的西黑冠長臂猿隻會留個背影給監測人員。蔣學龍表示:“盡管一些現代科技可以輔助西黑冠長臂猿習性的研究,但是人工觀測和種群調查對西黑冠長臂猿的研究依然不可替代。”
受疫情影響,去茶馬古道的游客少了很多,對西黑冠長臂猿感興趣的人更是寥寥無幾,林子多少有些失落。“其實追猿我也不圖啥,但是希望有更多人來關心關注我們這項工作。”林子說,這次調查可以讓更多護林員了解西黑冠長臂猿,也希望通過媒體的報道,讓社會更加關注西黑冠長臂猿保護。
臨別時,記者留下了每一位隊員的聯系方式,跟他們握手、或者擁抱——如果不是他們一路陪伴,記者絕對無法在哀牢山堅持三天。記者一行將睡袋、雨具和巡護服留給了調查隊員,他們未來還會需要這些裝備。
這是記者一次難得的採訪。這是林子他們的日常。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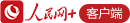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