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新春 話團圓
 |
 |
“年歲更替”,是時序歷法為春節確立的意義﹔“闔家團圓”,是煙火人間為春節賦予的深情。春節——這個對中國人來說尤為特殊的日子,人們總是期待著與家人一起度過。
千門萬戶曈曈日,家家團圓各不同。今天,我們與讀者朋友共話團圓,將這溫情種種,化作對新時光的禮贊。
——編 者
餃子的味道
賈飛黃
說到北方的年夜飯,繞不開的就是餃子。
年夜飯,要的是團圓。如此,從討彩頭的角度,似乎吃湯圓更加名正言順。可餃子偏不。它拍拍圓滾的肚皮,抖擻翻花的衣袂,喝一聲:“誰家過年還不吃頓餃子?”——是啊,憑什麼是餃子呢?或許唯有那當年新麥擀的面皮,最能彰顯五谷豐登的年景﹔唯有那葷素搭配、鮮亮扎實的餡料,最能吐露六畜興旺的喜悅。
抑或,也有現實的考量:包餃子是項不小的工程,男女老少各司其職、各盡所長,才能將這頓餃子包得又熱鬧又有滋味。人多好包餃子,人多就吃餃子。一頓餃子,既是團圓的由頭,亦是團圓的結果。當主婦們翻出一年不用的大面盆、大蓋帘,細細清洗時,耳邊便仿佛已經聽到新春的鐘聲,還有一大家子熱熱鬧鬧的喧嘩聲了。
品嘗餃子不分時令,但年夜飯的餃子獨有說道,講究自家現包,包出自家味道。百家餃子百家味,年夜飯餃子口味的傳承,暗藏在熱熱鬧鬧的年裡,像是一部廚房中的隱秘家譜。
奶奶家的過年餃子是酸菜餡的。從陽台的大缸裡撈酸菜,是過年餃子大戲的序幕。我們小孩子是愛看撈酸菜的,凡是有熱鬧的事小孩子都愛看。但當黃綠色的酸菜泛著刺鼻酸味,從大缸裡蔫頭耷腦探出頭時,小孩子又都被熏得尖叫逃開。很多年之后我才懂得,那刺鼻的酸才是家腌酸菜的醍醐味,在之后的悠長時光裡一再發酵,卻又無處可尋。
撈出來的酸菜沖洗幾遍,變得容光煥發,旋即被丟到菜板上,挑出肥厚適宜的大葉,剁餡的聲音在狹窄的廚房裡此起彼伏。酸菜芯,入味淺,酸甜剛好,被分給小孩子們當零嘴。我們舉著酸菜芯跑出廚房時,裡屋也已支起了方桌,發好的面團擺在正中。巧手的主婦圍坐,家長裡短地聊著,手裡卻不閑,揉面團,切面劑,等著餃子餡好了就可開包。
姥姥家的過年餃子則是素三鮮餡的。韭菜、雞蛋、木耳,唯有韭菜的存在感最為強烈。筷子頭大小的韭菜段,從拌餡人的袖套上蹭到小孩子的手上,又從小孩子的手上蹭到家裡的各個角落,仿佛是翠綠的洒金,讓大人無奈卻又忍俊不禁。
廚房裡的熱鬧,在包餃子的環節達到了高潮。一條流水線就此啟動,按劑子、擀皮、加餡、包制,一切有條不紊。大盆裡拌好的三鮮餡,碧綠的韭菜,金燦燦的雞蛋,如金玉滿堂,點綴著的黑木耳又添貴氣。一家人團圓包餃子,餃子也在圓形的蓋帘上團團圓圓,一圈又一圈,擠擠挨挨,如一朵肥美的白玉牡丹。我和表兄弟們有模有樣地幫廚,包出的餃子卻怪狀莫名,終於在大人“自己包的自己吃”的呵斥中哄笑四散。
奶奶家的酸菜餡餃子,總在席間上桌。濃郁的酸香中和了肉餡裡的油膩,蘸料不需加醋,隻用蒜泥醬油,伴隨著一聲聲“餃子就酒,越喝越有”的推杯換盞。這一刻,餃子既是下酒的好菜,也是解醉的主食,喧嘩談笑一浪疊一浪。姥姥家的三鮮餃子,多用於團圓飯的收尾。此時小孩子們早已耐不住桌上的高談闊論,抱著餃子碟坐在電視前,就著春晚把餃子吃了個津津有味。望窗外,華燈千萬,鞭炮聲聲令人心痒難耐……
后來,我客居他鄉,每每吃餃子,總是心有戚戚,對酸菜、三鮮兩種餡敬而遠之。一來,吃不到當年的味道﹔二來,不復當年熱鬧之景。提箸一人食,餃子似乎都涼得格外快。若是問我最喜歡哪種餃子,答案顯然也不可能是酸菜或者三鮮——那不是喜愛的味道,那是回不去的味道。
回不去,歲月流轉,人世更迭。家族枝開葉散,熱鬧的大團圓再難一見,而是散入萬家燈火,化作一個個中團圓、小團圓。家裡無人再腌酸菜,三鮮餡的組成和調味也是變了又變。年節的外賣餃子琳琅滿目,讓人眼花又有些茫然。似乎唯一沒變的,是我依然包不好一個餃子,而且如今連擀面杖和蓋帘,都不知道要去哪裡買了。
所幸,自家的小團圓,新春鐘聲敲響之時,母親還會煮一份手包的餃子給我。人少,吃得不多,餃子皮多用外面買的,餡料卻是自己調的,口味順著我們“小家”的喜好做了改良。酸菜餡餃子蘸上陳醋,三鮮餡餃子包了蝦仁,電視的音量撐起屋裡的熱鬧,一切似乎熟悉,卻又有所不同。
在這樣的氛圍裡,一家人將那枚年終歲末的餃子落肚,卻感到了久違的完滿。仿佛兩個農歷年的銜接處,補好了最后一片拼圖,時光決堤而去,自此奔流。
餃子的味道,正是團圓的味道。
圍爐時光
黃詠梅
我給父母買了一套煮茶爐具,放在陽台那張四方老木桌上。玻璃壺裡的六堡茶咕嘟咕嘟細聲煮著,濃釅的茶水一泡接著一泡,就像我們的往事,一串接著一串。春節團圓飯后,我們家就多了一個節目:圍爐煮茶。除了聊聊各自的生活,更多還是講那些我們共同經歷的過往。說起某些舊人舊事,便會有人不斷地補充,蔓延出另一些人另一樁事。往日的時間在我們的閑聊中如同一堆零散的積木,拼接出了一個百感交集的空間,空氣中流動著木炭的氣味、煮茶的陳香以及一種我定義為幸福的芳香。
我姐說,前些日子在街上碰到招弟,簡直認不出來了。招弟是誰?母親在心裡算了算,對我說,你那時小,大概沒什麼印象,招弟是梁大富的女兒啊。這個名字一下子點亮了我的記憶。在我讀小學之前,我們家住在市郊石鼓沖的一座小山上,上下山會經過幾戶本地人家。雖然我們家不是本地人,跟那幾戶相處卻很融洽,唯獨梁大富,無論大人小孩都不願走近。他總在屋門口的那個水龍頭下洗澡,全身上下僅穿著一條闊大的短褲,光天化日,也不避路人。父親告訴我們,梁大富是西江上的船員,大概走船的人在船上洗澡都那樣,上岸也改不了這個習慣。父親又說,其實他是個好人。
我們山上的那間小屋,屋背是山林。夏天的時候,不時會有蛇鑽進我們家。大概是我三歲的時候,梁大富幫父親對付過一條在我家飯桌底下吐芯的銀環蛇。銀環蛇有毒,父親認得出來,迫使他不敢輕舉妄動的是,當時我正坐在飯桌上,如同無知無覺的人質。母親隻能在門外朝山下喊救命。很快,光著膀子、穿著一條闊短褲的梁大富跑了上來,手上拎著一支粗竹筒。他先是朝蛇扔東西,將蛇的注意力引向自己。父母則在一邊喊話,安撫我,將我的注意力牢牢固定在飯桌上。等到那蛇游出桌底,梁大富幾步沖到近前,用力把竹筒准確地摁在了它的脖子上,瞬間制服了它。
這麼說來,梁大富還救過我一命。因為梁大富,我們連帶著又想起了一些舊事舊人。有意思的是,我們記起來的都是一些芥豆之事,誰誰誰對我們好,誰誰誰幫助過我們。仿佛在這種溫暖的氛圍裡,人的記憶也會自動篩選,過去的困苦都不值得一提。
一顆剝開的板栗放到了我的手上。“烤熟了,熱著吃才香。”母親挑出爐子上最先熟的那顆給我。我握著它,看看母親,又看看父親,沒頭沒腦地說:“謝謝爸爸媽媽,把你們女兒養那麼老。”一時間,母親不知道怎麼接話。我姐忽然拍了我一下,夸張地說:“我才沒老呢,別把我算進去。”我笑著攻擊她:“都更年期了,還不算老?”我哥接過話,表揚母親:“嘖嘖,老媽,你跟老爸真厲害,把兒女一個個養到了更年期。”大家都笑了。父親舉起一隻功夫茶杯敬母親,我們也跟著舉茶杯敬父母。
圍爐憶舊的溫暖以及那些紛至沓來的往事,使我們變得更加親密。在離開家的前一個夜晚,臨睡前,我坐在父母的床尾,將腳伸進被窩,跟他們說說話。東拉西扯,也談一些未來的計劃。這是我跟父母最親昵的時刻,這種時刻我會覺得自己變得很“小”,“小”到可以躺在他們懷裡,“小”到可以胡說八道一些話。“媽,要是時間能停下來就好了。”“媽,要是能回到小時候就好了。”這些無厘頭的撒嬌,我知道,是我在他們面前最大限度的鬆弛,或者某種虛弱的最大限度坦露。
清晨,天還沒亮透,我輕輕收拾好行李,要出門趕最早那趟高鐵。這次在我的堅持下,好不容易跟父母商量好,隻送出家門電梯口。不知道是因為昨晚聊太久,他們睡得太遲,還是因為安眠藥的作用,他們還沒醒。我悄悄走近他們床邊,他們的鼾聲在我聽來像一首歡快的曲子,節奏詼諧。我忍住了笑,將手探進被子裡,摸了摸床褥,暖暖的。我又想起了他們養的那隻大胖貓,轉身走向貓籠,伸手進去摸了摸墊在貓身下的棉布,暖暖的。貓的喉嚨震動出咕嚕咕嚕的歡喜的聲音。
在站台的前方,我等待的那輛列車呼嘯而來,而另一條軌道上,一輛徐徐開出的列車朝它迎面而去,過往交錯掀起了一陣強大的氣流,新的生活劈面而來。辭舊迎新,相比起來,好像人們更留戀那些辭去的舊,或者說,人們對那些舊的共同記憶愈發清晰起來。舊時光是過去時的,新生活是將來時的,如果不是人的記憶和情感在迎來送往,它們根本不會照面。
家庭“春晚”賀年歲
張朝林
去年春節前,父親分別給我們打電話,安排團聚事宜。他說,今年守年歲搞一個家庭“春晚”,讓我們每家都得出節目,多多益善。
父親是鄉村教師,教了一輩子音樂、唱了一輩子歌,退下來也閑不住,走哪兒唱到哪兒,還把村裡喜歡唱歌的老人組織起來,在老年活動室辦了個“夕陽文藝班”。老家河邊有一處院子,由父親母親照看。我們各有工作,平時很少團聚。可奔年守歲,雷打不動,再忙再遠,都要趕在除夕這天回老家,陪父母團聚。
院子裡,父親寫的金字春聯貼上了,紅燈籠挂起了,庭院的樹上、屋檐上也纏繞了霓虹燈,大客廳鋪上了紅地毯,背景牆上挂著父親書寫的“家庭春節聯歡晚會”,智能電視機周圍鮮花簇擁,麥克風架立在台中,大廳周圍也擺滿盆景和幾張圓桌,桌上放著水果點心。兒子忙著給爺爺調試每個節目的背景音樂和視頻畫面。媳婦陪母親在廚房裡忙活。母親樂呵呵地把涼菜、炒菜、蒸菜都備全,又揉了一團白面,剁好一盆餃子餡。
夜幕降臨,彩燈齊亮,歡快喜慶的音樂在大廳裡循環播放,年味在歌聲中飄揚。
二弟開車回來了,二侄女看見如此豪華的家庭舞台,高興得手舞足蹈,又塞給爺爺一個大紅包。二弟媳拿出一條厚厚的紅圍巾,圍在母親脖子上,樂得母親臉比燈籠紅。
汽車的喇叭聲響了,三弟一家到家了。三弟下了車,打開車后蓋,將出差在外地買的大包小包的土特產塞給了母親,把異鄉的年味帶回了陝南,惹得母親不停地說:“多了,多了!”
“家庭‘春晚’,正式開始!第一個節目,請欣賞視頻《綠山清水美家鄉》。視頻走起!”精神矍鑠的父親,嗓音不減當年。
伴隨著輕快的音樂,連綿的秦嶺、高聳的巴山、清澈的漢江以及家鄉的桃花源、千層河、甘蔗林、小溪流,都從畫面中跳出,天藍、雲白、草綠、水清、浪細、村美,大家屏住呼吸,凝神觀看。最后的畫面落到了我家院子的后花園上。真佩服有心的老父親,我們當場表示要把這個視頻存在手機裡,時時拿出來品味。
接下來的節目,是父親自己作詞、譜曲、演唱的一首《家鄉美》:“秦嶺巍巍巴山秀,清水漢江門前走,秦巴沃土真秀麗,時代春風吹大地……”父親邊拉著二胡邊唱,孫子蹲在旁邊舉話筒,兒媳婦們都上了台,起舞給父親助興。高昂的歌聲吸引鄰居鄉親們也趕過來看,大廳圍滿了人,母親一把一把地將糖果往鄉親們手裡塞。
三弟的拿手歌是《天路》。三弟繼承了父親的基因,嗓子亮,吐詞清。他唱得投入、悠揚、深情,把大家帶到了雪域高原。三弟前陣子恰好在高原地區出差,他把在那邊生活的感受融入這歌聲中。
輪到三侄女上場了:“我把一首《長大后我就成了你》獻給爺爺和在座的老師。”父親在一旁拉著手風琴給他孫女伴奏。
節目精彩紛呈,笑聲陣陣飄揚客廳。
自由表演環節開始了。圍觀的鄉親們也爭著上台亮相,說幾句笑話,來幾句祝福,許幾個心願,逗得大家開懷笑。
不知啥時候,母親又去廚房裡忙了。母親年輕時是隊裡文藝骨干。父親說:“最后一個節目,請內當家的上台。”母親不肯,大家起哄:“來一個,來一個!”她這才上了台。
“我們的家園,天地呈祥瑞,碧水繞青山,田野疊綠翠……”母親唱的是《幸福安康》,這首歌由安康人作詞,在安康傳唱極廣。母親唱得深情。一時間,鄉親們又圍過來,一起合唱。《綠山清水美家鄉》的視頻同時播放,父親吹笛伴奏。鄉親們邊唱邊舞,邊舞邊唱,一片歡樂熱鬧的氣氛。
突然,隻聽見外面煙花爆竹齊鳴。歌聲伴隨著爆竹聲,在家鄉的上空蕩漾,新村的夜空被耀得通紅。
玉龍雪山的祝福
陳洪金
窗外便是碧波蕩漾的滇池。清晨的陽光照著水面,看到的都是閃閃爍爍的“金子”,細碎地鋪滿了水面,有點晃人的眼睛。遠途而來的紅嘴鷗在水面上成群結隊地翻飛著。這些生靈一年一度來到溫暖的滇池邊,算是回到家了。它們情不自禁地發出叫聲,讓人聯想到一個遠行者回到村庄,隔著自家的樹籬,向著鄰居們親切地打招呼。
春節將近,我還在昆明參加一個臨時通知的會議。滇池與會場,隻隔著一條街。扭頭看向窗外,除了水面上的紅嘴鷗,還有匆匆而過的車流。時間已經臨近年關,那些車子似乎也有些著急,應該是在趕赴回家的路。
會議結束,我等著同來的朋友一起坐車回麗江去。匆匆吃了午飯,我們就匯入高架橋上滿滿當當的車流中,一路向著楚雄、大理、麗江的方向飛奔而去。我們要在太陽落山之前回到麗江,回去跟家人團圓,迎接新一年的到來。
越是心急,越是顯得路途遙遠。車過楚雄,遠遠地看見楚雄城裡高高的福塔,在心裡對自己說:走了大約三分之一。車過大理,遠遠地看見蒼山與洱海扑面而來,又在心裡對自己說:走了大約三分之二。車子穿過隧道,麗江城在一瞬間映入眼底,終於暗自喜悅,不禁輕嘆:終於回到麗江了。臨近黃昏時分,陽光照得麗江城一片金黃。麗江古城、獅子山、福慧路,這是回到麗江的人們第一眼看到的最為熟悉的場景。此刻,它們被欣悅的目光鍍上了一層淡淡的暖色,仿佛也在准備收拾好心情,迎接春天的到來。
回到家裡,整個小區已經籠罩在橘黃色的燈光裡了。女兒穿著一雙狗熊形狀的拖鞋,身上套著一件肥肥的毛衣,手裡卻在忙著裁紙、折紙,然后鋪展開來,蘸了散發出濃濃墨香味的墨汁,用她那娟秀的歐體字,在紅紙上慢條斯理地書寫春聯。我推門進去,她早已不像小時候那樣對父親的回家感到驚喜,只是抬起頭來,招呼我一聲,然后繼續埋頭寫她的春聯。
燈光照著她的身影,頓時感覺時光荏苒。幾年前,她還圍繞在我身邊,跟我一起去街上買了春聯,再貼到家裡一扇扇門上。轉眼間,她的身影穿過初中、高中、大學的課堂,回到家裡,自己買回紙張,拿出自己創作的春聯內容,一筆一畫,在紅紙上寫下對這個春天的祈願。不知不覺中,她寫出來的對聯鋪滿了客廳,處處都晾晒著墨跡未干的祝福。隔著窗戶,抬眼就可以看見遠處的玉龍雪山。山上的積雪閃著銀光,仿佛是嵌在窗子上的一幅水墨畫。雪山與春聯彼此映襯著,讓人感到舒適與恬靜。
一覺醒來,清晨,驅車往北,向著玉龍雪山腳下的田野而去。田野裡,麥苗正在冬春之交的薄霜裡慢慢恢復生長。麥田裡,一種叫作麥藍菜的野菜,也在漸漸變暖的天氣裡伴隨著麥苗生長。在我的故鄉永勝縣三川壩,每到春節的時候,鄉親們都喜歡用這種野菜腌制酸菜。作為對家鄉習俗的懷念,每年除夕前到玉龍雪山腳下的麥地裡採摘麥藍菜回來制作酸菜,便成了我這個新麗江人的新習俗。
下午,冬日暖陽讓人渾身舒暢,掃陽春又開始了。從城外村野裡砍一棵竹子剔去竹枝,隻留下竹尖上的幾簇葉子,做成了一個長長的掃把,伸向高高的屋檐,掃去一年積下的蛛網、灰塵、雜草,以及郁悶和病痛。掃完陽春,借著用過的竹竿,鋸下一截竹子,再仔細地把竹筒剖成竹條,削去棱角毛刺,再用砂紙打磨,幾雙素雅的筷子就這樣做成了。每一年的除夕,嶄新的筷子散發出竹子淡淡的清香,加入筷簍裡,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習慣,又在這種久違的清香裡傳遞到了新的一年。
夕陽下沉,暮色再一次降臨,街上開始傳來零星的鞭炮聲,已經有人忍不住節日的喜悅,開始在暮色裡提前燃放焰火,夜空被照亮。玉龍雪山在不遠處,靜默地注視著麗江城……
版式設計: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24年02月10日 07 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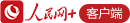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