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怒江每翻一座山,學校都不同

下雨了,學生排著隊去食堂吃午飯。

下雨了,一位老師帶學生在室內上體育課。

小學六年級的教室裡,擦除了黑板報的內容,隻留下小升初考試的倒計時。

下課了,學生在操場上打乒乓球。

一所學校沿著山勢階梯形建設。
6月中旬,正逢雲南的雨季,眼前的山體塌方還在持續,碎石不斷從山上滾下來,掉在219國道的柏油路面上。我坐在越野車上,車輛碾過塌方后還沒清理完成的碎石頭路,沿著怒江往峽谷的深處走。嘩啦啦的雨聲與怒江奔騰的咆哮聲交錯著,襯得兩側那些陡峭又插入雲霄的山幽深神秘。
這是我第一次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出發前,一位瀘水市政府官員告訴我,“瀘水在拿最好的平地建學校。”他還說,瀘水市政府教育支出佔比最大,保証老師收入。我很好奇,在邊境的縣城,花錢開辟的小學校園,花錢留住的鄉村老師,能給鄉村教育帶來什麼改變?
當我拐過上百道彎,最終抵達瀘水市、福貢縣、貢山縣的邊境小學時,答案才慢慢顯現出來。
1
4所邊境小學建在層層疊疊的高山深處,在中國地圖“大公雞的屁股”邊上。
做記者好幾年,我也採訪過一些東西部學校,這些邊境小學硬件設施絲毫不遜色於大城市的小學。距離中緬邊境隻有兩公裡的瀘水市片馬鎮國門小學,在大山邊上給學生開辟了3個標准尺寸的籃球場、1個羽毛球場、4個乒乓球桌﹔建在怒江邊上的福貢縣臘竹底完小,順著山坡的地勢,依次建起了宿舍、教學樓、圖書館、體育場,還有2個戶外游泳池。
學校還給學生開設了古箏課、手鼓課、合唱團和各類體育活動社團。舞蹈教室的地板用的是柔軟的特殊材質,讓學生能放心地赤腳跳舞。
一位邊境小學的校長說,學生收到外界捐贈的書包和文具太多了,最多一個人能收到三四個書包,用不完。
大多時候,這群小學生的校園生活是輕鬆的:每天能睡11個小時,午餐和晚餐后是游戲時間﹔食堂有葷有素,比一些學生家裡做的飯更豐富﹔許多同學說,學習是輕鬆的事,沒聽過要“卷”。雨季是這群孩子愁緒的來源——下雨了,就不能去操場上玩了。
一些邊境小學還會接收來自緬甸的學生。一位校長指著走廊上拿著水杯准備接水的女孩說,“這一個學生是緬甸籍,正在讀五年級。”以前,還有緬甸籍學生坐公交來中國上學。還有一位17歲的學生,以前在緬甸生活,現在在邊境小學的一年級讀書。
一位當地教體局的工作人員介紹,他們的學生普遍享受14年免費教育,從幼兒園兩年直到高中、高職﹔如果貧困學生考上大學,能享受各種補貼,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每一年,從怒江州考上大學的學生,絕大多數是憑借少數民族能歌善舞的優勢,以藝術生、體育生的方式。要和大城市的、小縣城的孩子拼文化課,怒江州的學生沒有優勢。
一位校長說,學生從小習慣爬坡,不缺體能,也不缺體育設施和時間,但缺體育技能。
在一個下雨的早上,我旁聽了一節上海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在邊境小學開設的運動夢想課,因為天氣限制,體育課挪到夢想中心教室進行。老師把教室裡的桌椅都搬走,騰出空間,帶領30多個學生在室內跟著兒歌跳操。
既然學生好動,體育時間能保障,為什麼還要在邊境小學提供運動課?基金會的工作人員說,基金會給學校提供針對青少年發展需求研發的補充類體育課程和教學視頻,希望讓非專業體育老師能對照教案教體育課,不會出錯﹔同時捐贈一些輕量化體育器材,也能讓孩子強身健體的同時,享受安全、高效、有趣的體育課。
這裡邊境教育的復雜性在於,沿著怒江,每翻一座山,學校面臨的困難都有所不同,沒有統一的解法。即便是培養學生體育技能這一件小事,每所學校的情況都不一樣。
靠近縣城的鄉村小學,很難找到合適的體育老師,因為有體育技能的人更願意去縣城當健身教練,工資高﹔一些學校即便引進了音體美專業的老師,由於主科老師少,無法做本專業的事,隻能改教語數英﹔還有校長說,有時流動調配來的老師,擅長的專業不是學校最需要的科目。有所小學老師數量太少,老師不得不既教語數英,也教音體美。
我想起幾年前探訪過的北京市中心一所小學,就在胡同和四合院邊上,由於能用的土地空間太少,給學生鋪設的跑道不得不從校門口開始,一直延伸到圍牆邊上。校長擔心學生會受傷,在圍牆上貼軟墊。
這裡和北京的小學不同,北京小學的體育課缺的是土地,是空間。而這些邊境小學不缺土地、設施、器材,它們的體育課受到所處的地理環境、學校條件制約,問題更加復雜,其中蘊涵著教師資源錯配、教師稀缺的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決。
同樣,這些邊境小學也建了醫務室,卻招不來校醫,建了心理輔導教室,卻沒有專職的心理老師。一位縣城教體局的領導說,學校的校醫大多是兼職,不夠專業。每次學生生病,老師得自掏腰包送往縣醫院就醫。
還有所學校至今仍在堅持疫情防控,要求師生戴口罩。校長解釋,最近的縣醫院距離學校44公裡,車程一個多小時,一旦傳染病暴發,學校無力及時地把大批孩子送往醫院。
2
在這崇山峻嶺的深處,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僅在托起一個小孩,還在為一個家庭托底。由於居民住得散,住所又離學校遠,這裡的孩子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寄宿,每周或每兩周的周末回家,幾個住得鄰近的學生家長會拼車到校門口接送。
老師說,一年級的孩子最難帶。倒不是因為調皮,也不是因為生活不能自理,而是尿床。有些老師夜裡得掐著點挨個叫一年級學生起床上廁所。
還有些孩子沒有從小養成每天刷牙、經常洗澡的衛生習慣,經常生病。在山區,學生生活用水依靠從山上流下的泉水,水泵水壓小。臘竹底完小的洗澡間不能讓所有孩子定期洗澡,隻好開辟兩個游泳池,輪流安排不同年級學生去洗澡、游泳,保証學生隔兩三天能洗一次澡。
據一位長期關注鄉村教育的公益人士觀察,有些外出務工的父母為了補償孩子,每個月會給留守兒童寄回大筆零花錢,卻沒有教孩子怎麼消費。孩子收到錢往往一兩天就花光了。他們擔心,即便這群留守兒童長大了,外出打工,也很少有好的理財觀念。
在這裡,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都壓在學校和老師身上。一些家長把孩子甩給學校后外出打工了﹔有的父母離婚,家庭管孩子少,全靠學校托底。
當老師問及學生的煩惱時,極少有人提到物質上的渴求。有個孩子說:“爸爸媽媽離婚了,我很不開心,因為我很想媽媽。”說完,他把頭埋在課桌上哭了一陣,旁邊的同學輕輕拍打他的肩膀以作安慰。
我家訪的家庭,母親很少關心孩子的功課,“孩子的功課我也不懂”,也不太關注孩子的情緒變化。有些學校很少給孩子布置周末作業,因為老師知道,孩子回家后,大多要幫父母干農活。
這裡的老師教完課后,還得管生活。一位校長說,為了避免學生發生沖撞,每次集中體育鍛煉時,要派十幾個老師在學校不同角落看守。
一所邊境寄宿小學的師生比低,學校派兩個老師負責一個班級所有科目的教學和所有學生的生活。一位英語師范專業畢業的老師,如今改教語文、道德與法治、美術、書法,每周要上24節課,還要兼顧學校的管理工作。
上海市派到怒江州幫扶的小學老師,因為師生比低,很不適應邊境小學的工作節奏:課時比上海多3倍,晚上查房到12點多,第二天早上還得上1-4節課。
如今,大城市的中小學也講究全科教育,要在一道試題裡,塞入多個學科的知識,還有的機構開辦“體適能”課程,要精准地提高幼兒園、小學階段的學生運動水平,並在體育課上全程用英語與學生對話。
但這與邊境小學的全科教育不一樣,前者已經進階到多學科融合教育,后者更多是在老師稀少、錯配的條件下不得已的選擇。
在開放二孩、三孩政策以后,一位校長明顯感覺到,老師增長的速度明顯趕不上學生增長的速度。一所即將擴招的完小,計劃把兩間老師辦公室改造成教室。
“雙減”政策開始后,雲南省允許一個學生收400元課后服務費,但邊境的學生大多家庭條件差,收不了錢,絕大多數學校的課后服務不收錢,反而增加了在職老師的負擔。一位教體局工作人員說:“本來老師可以5點下課,現在要課后服務到6點多。”
有些學生跟不上新課標的內容。比如英語課,學生得由傈僳語母語,轉變為普通話,再翻譯成英語,英語老師上課得花更多時間,先讓學生用普通話表達,再用英語說。又比如,很多小學生沒有跨出過怒江走出大山,很難理解課本裡提到的磁懸浮列車。
不僅是學生,就連老師在大山裡待久了,教學質量也在原地踏步。福貢縣一所學校好不容易拿到了100多萬元的培訓費,校長卻犯了難,要是組織一波老師外出培訓,正常的教學秩序就會受影響。
兩個小學老師包攬一個班級的模式,也容易出現問題:如果其中一人請假,或外出培訓,另一位老師得從早到晚地上課。一位校長說,以前,外出培訓的機會都給了那些邊緣的、上不了主科的的老師,但那些老師即使接受培訓,回到學校,也無法帶動提升教學質量。
3
219國道是通往怒江大峽谷深處的幾個縣城最重要的一條路。從我探訪的4所學校來看,距離城市越遠的邊境小學,留守兒童的比例越低,輟學率也低——由於路途遙遠,父母大多依賴政府組織務工,靠著政府組織的包車統一外出,學生要出去一趟也麻煩,很少有學生輟學外出打工。
與此同時,這些遠離縣城的邊境小學留不住鄉村老師。老師更傾向於在縣城附近、交通便利的鄉村小學教書。這也是再翻幾座山,學校情況不太一樣的原因。
這側面反映出“走出大山”的難度。一位從上海來怒江州挂職的官員說,從他所在的貢山縣去一趟昆明開會,光在路上就要花兩天。
一位父親說,在生小孩前,他們夫妻倆在深圳打工,每個月能賺8000元,有時能賺1萬元。但陸續生下兩個孩子后,夫妻倆擔心村子裡經常有人喝酒、鬧事,選擇留在村子裡的茶葉加工廠,陪伴孩子長大,等到孩子上初中,有自理能力,再外出打工。
他的女兒目前讀小學三年級,但這位初中畢業的父親要幫女兒輔導功課時,也會覺得力不從心,“現在小學的課程越來越難了,我教不明白”,但他決心,隻要孩子願意讀書,“想上到什麼程度,我一定努力供到什麼程度。”他想把孩子推到更遠的地方看看,走出大山。
“走出大山”這4個字,反復出現在家長、老師、校長的口中。
一位校長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和怒江州以外的學生一樣,考高中,上大學,改變大山裡落后的傳統觀念,而不是隻接受了義務教育就回到農村。
一位老師說,他不敢想太遙遠的目標,隻要學生能走出大山,改變觀念,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就很好,但如果學生將來畢業后願意回到家鄉,用自身經歷帶動更多孩子走出困境,那就最好。
貢山縣一位校長說:“我長期住在山裡,這座山很高,后面那座山比這座山更高,人在裡面就像‘井底之蛙’。”有一次大雪封山,她被困在學校5個月,等到隧道通了,她坐車出門採購,遠遠看到了縣城,忍不住說:“全部人下車,大聲地叫吧。”
不久前,她給六年級學生開動員會,聲情並茂地鼓勵學生,“隻有讀書能改變命運”。
一位教體局工作人員說,他來怒江教書19年了,本來想通過教育影響下一代的觀念,但是一些人落后的觀念根深蒂固,讓孩子讀完初中、高中就外出打工。這一度讓他感覺失落。
4
在探訪過程中,一位在學校幾個科目都考年級第一名的女孩,突然見到很多陌生人,哭了。她說,幾個月后,她會去縣裡讀初中,擔心和那些在縣城讀小學的孩子合不來。
“我們的學生普遍不太自信,即便在學校表現很好,換了一個環境,會變得扭扭捏捏。”一位校長說。
這些邊境學生的教育,正在受到多方的重視。2021年3月12日國家公布“十四五”規劃,提出要在邊境縣(團場)建設100所國門學校﹔當地教育局和學校不斷吸引優秀老師資源,提升教學軟實力﹔像真愛夢想這類的社會公益組織也開始將目光移向邊疆教育,探索將先進的教學理念引入邊境小學。
一些機構組織西部校長去東部培訓,一位邊境小學校長去了青島,旁聽了一節英語課后,感慨道,“這裡的學生英語真好。”組織培訓的工作人員說:“我們不是讓你來看學生講英語,而是讓你來看看以學生為中心的管理理念。”
在上海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的前期調研中,他們發現,邊境小學的學生自主性、眼界、自理能力和語言能力有待提高,而且,邊境的大部分小學生用知識改變命運的意識不強,缺少對未來的想象,他們希望孩子們“學會處理人與未知的關系,成長為求真、有愛的追夢人”。
去遠方,是許多城市家庭為孩子選擇的“開拓眼界”的方式之一。在大城市的課堂上,當老師提到肯尼亞的動物大遷徙、雅典的神殿、東非的大裂谷,總有學生站起來,描述他們親臨現場看到的細節。
我採訪過一個中德青少年藝術活動的組織者,他每年暑假會組織有樂器基礎的中國小學生去德國知名的藝術廳,和德國的同齡人交流,給德國的民眾表演節目。這群學生還會探訪德國的博物館、圖書館、藝術展。一位帶隊的老師說,學生在無形中提高了自理能力和藝術視野,會變得更加自信。
但對於邊境的學生,這樣的機會實在太少了。我家訪的一位小學生,被在外打工的二姨帶著去西雙版納旅游,看到了“野象發怒”的模樣。但她的父母說,光靠父母二人的力量,很難帶孩子去更遠的地方旅游。更多學生連西雙版納的野象都沒看過,去過最遠的地方是縣城。
上江鎮中心完小的校長發現,鼓勵學生走出去的重點,是培養一項愛好,能陪伴終生的愛好。
他舉例,學校有位四年級的學生自從愛上踢足球,就變得特別勤奮,明明生病還要去戶外上體育課。老師引導他:“以后要去大山外面踢足球,文化課也得跟上。”這位學生為了這個目標,其他科目的成績進步很快。
校長說,這個小學生給了他新的啟示,“隻要有一項愛好,學生的各方面都會提高。”為此,他特意開設很多社團,讓每個孩子都有參加的項目。
他最新的教學目標,是讓這些學生找到能讓心靈棲居的地方,長大后不能當“空心的人”。
還要把家長也拉進教育的隊伍裡。貢山縣一位校長記得,5年前,學校第一次開家長會,500個家長隻來了100多人。她鼓勵家長要在家養好豬、養好雞,不能完全甩手把孩子扔給學校,還應該讓學生與山外面的世界有更多連接,鼓勵家長帶孩子去喝奶茶。
不久后,有個家長趁著學生周末回家,特意煮了雞蛋,還殺了一隻雞,說是校長教的,“要為祖國干一件大事”。
2023年,貢山縣這個學校再次舉辦文藝晚會,那天走進學校的家長站滿了整個操場。(魏晞)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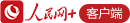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