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居是初代“搭子”,滿載“附近”的力量

《小巷人家》劇照。出品方供圖
飯搭子、運動搭子、學習搭子、旅游搭子……如今,年輕人之間盛行“搭子”關系,主打一個精准陪伴。很多關注和言論言必稱“這屆年輕人”,但誰又不曾經是個年輕人呢?“搭子”這個東西,其實有一個初代版本,那就是工友兼鄰居。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也就是我的父輩還青春正好的時候,18歲進“大廠”當工人,是當時年輕人最流行的選擇之一。那時候,工友是一種穩定的社交關系——能一直維持到退休﹔與此同時,工廠還分房或給宿舍,年齡相近的一批工友成家后,往往會住在同一片小區。
他們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做飯、一起吃飯,有了孩子,又成了“育兒搭把手搭子”“親子游搭子”……現在看來,這是一種脫離了血緣和地緣的關系,具有鮮明的“自我選擇”的色彩。
我的父母是20世紀60年代初生人,在革命友誼升華之后,和另外幾戶同樣剛組建的小家庭,住到了同一個“牆門”。“牆門”是一個吳語詞,類似北方的四合院,古代是一個家族聚居的宅院,后來慢慢成為幾家人一起居住的小院。“牆門”的要義在於,裡面沒有親緣的若干戶人家,關上大門,幾家人就成了一家人。
“牆門”是一個在我記憶中模糊不清——畢竟我家在我3歲時就搬離了,但在相冊和父母的回憶中熠熠生輝的地方。最近,他們追一部熱播劇《小巷人家》,又打開了這段塵封記憶,劇中的主人公還是他們年輕時的模樣。
《小巷人家》講述了20世紀70年代末,蘇州某棉紡廠改造了一條小巷,分配給職工做宿舍。溫婉的黃玲和潑辣的宋瑩,兩家人分到了同一個小院,開始了幾十年的鄰居生活。劇中沒有驚濤駭浪的大起大落,但在細水長流的娓娓道來中,觀眾眼淚的滑落可以在任何不經意的瞬間,並不是因為悲傷,而是回憶涌上心頭又堵在喉嚨。
我在記事之后,聽父母回憶起“牆門”的生活,被反復提起的並不是純粹的喜劇或悲劇,而是那些苦中作樂。據說,我出生的那一年,暴雨不止,錢塘江的水漫了出來,處在低窪地的“牆門”也進了水,於是幾家人先在大門口筑起“堤壩”,再用上最大的臉盆,拼命往外舀水﹔還據說,當時幾家人共用一個廚房,那個衛生條件簡直不宜細說,但不妨礙其中一家的男主人練就一身廚藝,后來改行成了大廚……
我們總是希望在一個屋檐下,找到與自己十二分投契的人,但好的關系,是可以始於“相同”而能包容乃至學習“不同”的。在《小巷人家》中,黃玲和宋瑩的性格和家庭關系截然不同,但在初印象的“看不慣”后,兩個智慧的女性很快就發現了對方的閃光點。
黃玲的丈夫庄超英愚孝,外人也給黃玲貼上了“賢妻良母”的標簽,但和宋瑩做鄰居后,黃玲開始有了拒絕的勇氣,而且她發現,拒絕后,事情也沒有變得多麼糟糕。宋瑩夫妻原本對兒子林棟哲的學業不管不問,黃玲一家規勸鄰居:“今非昔比,時代在變化,國家政策也在變。”宋瑩一家聽進去了,兒子硬是從“學渣”考進了上海交大。
現在有一個流行詞——附近,是人類學家項飆提出的概念,他還希望年輕人能夠“重建附近”,重新認識周邊和安頓自身。
當我們沉醉於虛擬世界的信息繭房時,從更加真實的附近找到生活的存在感,與鄰居的相處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不知道從何時起,與鄰居有關的新聞往往不太愉快:“鄰居家門安裝電子貓眼侵犯隱私”“鄰居上門挑舋丟刀進屋”“鄰居欠電費小區集體停水”……零星個例被集納就顯得充滿了戾氣。
然而在城市中,尤其是對獨自到異鄉打拼的年輕人來說,鄰居其實是離你最近的人。我剛畢業時,獨自租住在北京北五環外的一個小區,有一天穿著睡衣出門丟垃圾,風吹上了虛掩的門。沒帶手機沒帶鑰匙,我思慮再三,用最傳統的方式,敲開了從未謀面的隔壁鄰居的門。對方是一個姐姐,我說明情況,她毫不懷疑,幫我叫了開鎖師傅,還主動借了我開鎖費,問兩百夠不夠。那一刻,她是電她是光她是唯一的神話。
鄰居之間的溫情,曾有過很多值得記入民間歷史的故事,是文藝作品的富礦。我們需要大江大河,也需要小巷人家,不同視角的敘事,其實共同構成、一起指向同一個主題,就是美好生活。而尋找生活的“搭子”,不妨從“附近”開始。
后來,父母所在的工廠經歷了私有制改革,“牆門人家”也到了離別的時候﹔再后來,小城日新月異,“牆門”也被高層樓盤取代。但很多年過去了,每年過年,父母“那屆年輕人”仍然會聚會,仍然會說起那場大水、那個廚房,老花的眼睛裡閃閃發光。
就像《小巷人家》的主題曲《消失》中唱的:“記得那個地址,我們仍是那個樣子。”(蔣肖斌 )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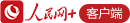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