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弒”在古代政治倫理文化中的語義變遷
中國古代政治倫理文化強調名分,君臣上下用語等級分明。但后世為人君所專用的一系列稱呼並非自古已然,而是隨著時代變遷而不斷演變。如《日知錄》說:“漢初,人對人多稱臣,乃戰國之余習。”“人臣有稱人君者”,亦可被稱“萬歲”。“弒”字同樣如此,細察其語義變遷,亦非自始即指臣殺君,而是自有其演變歷程。正如陳寅恪指出的:“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從“弒”字的語義變遷,可以管窺中國古代政治倫理文化變遷的軌跡與圖景。
一
“弒”作下殺上之專稱,此為人們熟知的文史常識。然而,秦漢時期的文獻卻呈現出“弒”含義的不同面相。
秦漢時期,“弒”並非均指下殺上,上殺下亦可稱“弒”。《公羊傳》載“昭公將弒季氏”,昭公為國君,季氏是臣下,此處便以“弒”字指上殺下。何休受后起語義影響而曲為之說:“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言弒。”驗諸王符《潛夫論》,亦有“桓魋不節飲食以見弒”之說,桓魋為宋國司馬,宋景公雖對其寵愛有加,但不至於視如人君,故何休的解釋實為牽強。另外,毫無君臣關系的互殺也可稱“弒”。如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公羊傳》《穀梁傳》述其死為“君弒”,即稱齊襄公殺魯桓公為“弒”。《史記》載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列女傳》稱公子負芻滅李園家為“宗族滅弒”。這些被殺者和殺人者均非君臣關系,卻皆稱“弒”。
此外,這一時期,下殺上也並非均稱“弒”。如《管子》曰“臣不殺君”,《墨子》曰“教臣殺君”,甚至以嚴君臣之防見稱的儒家著作,如《春秋繁露》亦屢稱“殺君亡國”“臣殺君,子殺父”。可見,秦漢時期尚未嚴格區分弒與殺,二者往往混用。
這一現象與《白虎通》的釋義相應。《白虎通》曰:“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弒之。《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公羊傳》:“何隱爾?弒也”,熹平石經作“試”,可見《白虎通》不為無據。因此,朱珔認為:“弒本從試得義。”《釋名》:“弒,伺也,伺間而后得施也。”“試”意味著對結果沒有把握,“伺”意指因無把握伺機而動。《漢書》中“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其意指:甲伺機把閩越王殺死。因此,起初“弒”本無名分限制,隻表示“試殺”或“伺殺”之內涵,傾向於指涉行為過程,與指涉行為結果之“殺”有異。鈕樹玉認為弒“不為悖逆造文”,不為無見。
二
以下殺上為“弒”的名分性表述,最早見於《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弒”,但《文選注》卻引作“殺”。因為無法排除后世改訂的可能,《左傳》原作何字實難遽定。《國語》中“下虐上為弒”亦然。最早明確“弒”字下殺上涵義的是《說文解字》:“弒,臣殺君也。《易》曰臣弒其君。”許氏與《白虎通》同引《周易·文言傳》,卻省略“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一句,或是意圖消弭弒之“試”“伺”本義﹔同時,他又將以往典籍中各種類型的“弒”字用例都加以遮掩,僅以“臣殺君”為“弒”字全部內涵。
當然,許慎之說並非由來無據,“弒”於此前已附著了名分色彩。許世子止誤殺許悼公,《公羊傳》稱“止進藥而藥殺”,承認他有殺君之實,但因他本無殺君之心,故又稱其“不成於弒”,在倫理上免除其罪責。於此,“弒”與“殺”便有區別:“殺”是行為結果,而“弒”則有從倫理名分予以定性的意味。段玉裁注《說文》,以“述其實則曰殺君,正其名則曰弒君”區判弒與殺,於此有其合理性。
《說文》的解釋預示著“弒”字語義政治倫理化的趨勢:從本指無名分限制的“試殺”,逐漸趨向於隱含倫理批判的下殺上。因此,阮元說:“君臣父子之義定,則此字之書法讀法亦定。”俞正燮也說:“弒者,畏忌之不敢直殺也。古語上下共之,秦漢以后始定於一。”當然,許慎雖確定了“弒”的名分意義,卻未對其外延作明確限定:“弒,臣殺君也”,隻說明凡稱“弒”均指臣殺君,卻未明確臣殺君是否均稱“弒”。“弒”字語義此后的發展,在政治倫理意識的主導下進一步明確化。
三
俞正燮雖稱“弒”之倫理內涵,“秦漢以后始定於一”。事實上,歷史錯綜復雜,絕非邊界分明,“弒”字倫理內涵之確定,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到隋唐時期,同一古籍不同版本之間,仍普遍存在弒殺混用現象。
《經典釋文》訓釋先秦經典,每謂“殺,本或作弒”或“弒,本又作殺”。可見陸德明所據底本與別本多有弒殺異文,此類異文所見共25處。對此,陸氏僅以“或作”“又作”注明,而不以“當作”訂正,說明他一定程度上接受這種差異。在開成石經中,《春秋》同一則經文於《三傳》之間,亦存在弒殺異文。如《公羊傳》僖公九年經“晉裡克弒其君之子奚齊”與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穀梁傳》《左傳》均作“殺”。弒殺異文,《春秋》一字褒貶如何可能?可見與陸德明一樣,其中均體現對弒殺混用的寬鬆態度。
由此可見,弒殺混用的語用規則,仍持續至隋唐時期。但與漢代之混用不同的是,此時之混用隻限於下殺上,而上殺下則隻書“殺”,不再見書“弒”之例。這是對許慎“弒”字涵義倫理化論述的呼應。
文獻傳抄難免“魯魚亥豕”,對古籍弒殺異文,段玉裁歸結於“轉寫訛亂”。他據其所歸納的古音韻部立論,認為弒殺古音不同部,不相假借,從而判定凡混用必訛誤。此說雖頗有附和者,但亦遭不少反對之聲。朱珔、馬敘倫便從音韻立論,對段說提出疑問。段氏以后,郝懿行、朱一新等學者仍相信“弒殺古通用”。轉寫訛誤固然無法排除,但當版本差異成為普遍現象時,僅以訛誤解釋顯然難以自洽。弒殺異文的普遍性,說明它在語用上具有合法性,並非全出於失誤。對此,阮元之說值得參酌:“《三傳》之字或有異同,否則以弒為殺,即失《春秋》第一大義。《三傳》大儒不應不嚴一字之誅而錯不較也。”倘若其時弒殺區分如段玉裁所言那般嚴苛,儒者傳抄經傳時不應不嚴加校勘,以致出現大規模異文。段玉裁以唐代以后更嚴苛的“弒”字語義審視唐代以前文獻,如此難免處處捍格。
四
唐代是“弒”字語義變遷關鍵而微妙的時期。一方面,弒殺仍然混用,另一方面,“弒”之語義進一步突出其名分性。其間,劉知幾起到關鍵作用。劉知幾說:“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以)上皆謂之弒,卿士已(以)上通謂之殺。”他對《春秋》“晉裡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一類說法提出疑問:“夫臣當為殺,而稱及,與君弒同科。苟弒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劉氏之意非常確定:弒—君,殺—臣,一一對應,界限森嚴,絕不混用。這種對弒殺嚴格分判的政治倫理態度,代表“弒”字語義此后的發展。
考今本古籍,除若干模棱兩可之處,下殺上多統一書“弒”。這種整齊感便可追溯至唐儒的刻意改訂。唐以前,經籍多有“殺君”表述。《經典釋文》記載了73處“殺君”表述,其中25處底本與別本存在弒殺異文,另外48處底本作“殺”而不載別本。至開成石經便對這些“殺君”表述予以統一化處理:25處弒殺異文僅1處從“殺君”,其他均從“弒君”﹔48處無異文之“殺君”則均直接改作“弒君”。此前版本的“殺君”表述便淘汰殆盡。史稱石經“立后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后世校訂經籍卻往往據為權威。
唐代以后,針對古籍“殺君”表述的訂正,仍曠日持久地開展。如對《春秋繁露》《公羊解詁》的“殺君”表述,凌曙、陳立等便訂正曰“殺當作弒”。其甚者竟至“凡殺字皆改為弒”,將減殺亦誤改為“弒”。這種嚴苛態度,與陸德明不辨弒殺,隻注異文的做法迥異。陸氏對弒殺的態度,也被后儒批判。段玉裁斥其絕無裁斷之識、不合正誤之法,並說:“此何等大事,而謂聖人垂世立教之書本無一定之字,可以蒙混書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春秋》書弒,以立萬世臣道之防也。”這是唐代以后訂正古籍“殺君”表述的出發點,此中彰顯著鮮明的政治倫理。周壽昌毫不諱言地指出:“史筆之嚴全恃此字,不得以古殺弒兩字多相混遂不加勘正也。”盧文弨也道明其中原委:“凡經典弒多有作殺者,后人往往以名分改之,故與陸氏本異。”
思想史的演變情節十分復雜,每條思想線索的節點並非迥然分明。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清晰地看到,從許慎到劉知幾到唐以后儒者,關於弒的名分性表達逐漸從弒殺混用中掙脫出來,最終成為關於弒的權威性詮釋。若僅從傳統語言學的范疇去解釋這個變化,可能不得要領。 (作者:朱麗師、蔡智力,分別系湖北大學文學院講師、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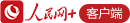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