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分野,為何存在“兒童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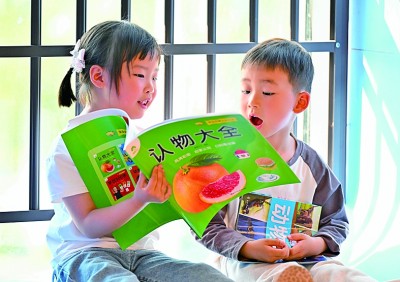
小朋友在安徽亳州市譙城區新華書店裡閱讀。劉勤利攝/光明圖片

在江蘇常州市新北區銀河幼兒園,家長和小朋友一起閱讀書籍。新華社發
【學術爭鳴】
尤瓦爾·赫拉利認為,隻有人類的語言能夠討論虛構的事物。“兒童文學”“成人文學”都是虛構的事物,是我們頭腦裡的抽象觀念。我們用不同的語言,對不同的抽象觀念作出命名,這本身就是一種區分。如果“兒童文學”“成人文學”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已經約定俗成,被人們所普遍使用,那麼,兩者之間就必然存在著藝術上的分野。論述“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存在分野這一問題,我們可以進行歷史的考察和理論的論証。
人類的某一個重要的觀念,必有它孕育和發生的歷史。在任何國家,“兒童文學”這一觀念都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在從古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過程中發生的。在中國,“兒童文學”發生的過程,就是一個與成人文學進行區分的過程,第一步就是將“兒童”與“成人”區分開來。魯迅說,對於兒童,“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於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周作人則說:“我們對於誤認兒童為縮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對,就是那不承認兒童的獨立生活的意見,我們也不以為然。”五四時期,以周氏兄弟為代表的“兒童本位”的兒童觀有兩個內涵:一是推倒“父為子綱”,主張兒童與成人有平等的人格﹔二是認為兒童在生理、心理上與成人有很大的不同,對此應予以相當的尊重。有了將“兒童”與“成人”區分開來的這第一步,“兒童文學”的誕生才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在中國,最早提出“兒童文學”這一詞語,並對其進行觀念建構的是周作人於1920年發表於《新青年》上的《兒童的文學》一文。考察當時周作人、郭沫若、鄭振鐸等人的兒童文學論述,“兒童本位”是他們共同的主張,並以此劃分出“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的界限。周作人在《兒童的書》中指出:“兒童的文學只是兒童本位的,此外更沒有什麼標准。”郭沫若在《兒童文學之管見》一文中提出“兒童文學其重感情與想象二者,大抵與詩的性質相同”,但是他也揭示出“兒童文學”與“詩”(成人文學)“所不同者特以兒童心理為主體,以兒童智力為標准而已”。鄭振鐸在《兒童文學的教授法》一文中,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兒童文學和普通文學分別的地方有三點”,分別是“格式”、“意義”和“工具主義”。
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認為:“理論是我們撒出去抓住‘世界’的網。理論使得世界合理化,說明它,並且支配它。我們盡力使這個網的網眼越來越小。”要對“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存在分野這一問題作出更“合理化”的說明,我們必須訴諸理論性闡釋。
作為與“成人文學”存在分野的“兒童文學”,必得有其獨特的美學品質。關於兒童文學的美學特質,有不少學者作過論述,我則將其提煉和歸納為“四美”:簡約之美、朴素之美、輕逸之美和稚趣之美。
兒童文學最重要的審美特質,就是有著近於數學公式的簡約之美。這樣的簡約不是簡單,它並不與復雜性相矛盾,而是濃縮了巨大的豐富性,是以少少許勝多多許的簡約之美。例如湖南兒童詩人李少白寫的《回家看看》:“一手敲門/一手捧機/右手筷子/左手手機/嘴說再見/眼盯手機/回家看看/看看手機。”由於“娛樂至死”這一人性弱點,與網絡連接的手機正日漸侵蝕人自身的健全生活,使人性走向“異化”。《回家看看》就是以極為簡潔、單純的白描形式,直接觸及了時代的這一脈搏。它的思想不是哲學的思辨,而是詩性的感悟,但卻擁有一種思想的穿透力量。何謂“大道至簡”,何謂“真傳一張紙,假傳萬卷書”,可以由這首詩得到生動的說明。不只是童詩,在《活了一百萬次的貓》《失落的一角》等繪本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簡約之美。兒童文學正是因為簡約,才能夠更鮮明、更准確地逼近事物和生活的本質。
兒童文學的朴素之美,是經典兒童文學作家的共同追求。普希金寫道:“我對咱們那些瞧不起用朴素語言來描述普通事物,而以為為了把給孩子看的故事寫得有聲有色,就拼命堆砌補語、形容詞和毫無新意的比喻的作家,能說些什麼呢?……‘一大早’,這樣寫就蠻好,可他們偏要這樣寫‘一輪旭日剛把它第一束光芒投射在紅彤彤的東邊天穹’,難道說,句子寫得長就精彩嗎,喲,這可真是新鮮透了。”創作了中國兒童文學經典《小坡的生日》之后,老舍說道:“最使我得意的地方是文字的簡明淺確。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真正明白了白話的力量:我敢用最簡單的話,幾乎是兒童的話,描寫一切了。我沒有算過,《小坡的生日》中一共到底用了多少字﹔可是它給我一點信心,就是用平民千字課的一千個字也能寫出很好的文章。我相信這個,因而越來越恨‘迷惘而蒼涼的沙漠般的故城喲’這種句子。”
兒童文學之所以堅持自己朴素的藝術品格,是因為它對自身藝術“質地形色”的充分自信。由此我聯想起無伴奏合唱藝術,它不依賴任何樂器的裝飾,全憑天然本色的聲音,卻真正表現了歌唱藝術的極致。兒童文學也正是敢於進行無伴奏歌唱的藝術之大者。
兒童文學具有輕逸之美。法國詩人保爾·瓦萊裡有詩曰:“應該像一隻鳥兒那樣輕,而不是像一根羽毛。”正如瓦萊裡的比喻,兒童文學的“輕逸”,不是沒有分量,而是因其藝術形式的巨大力量,使思想變得輕靈,能夠展翅飛翔。比如,繪本《我的爸爸叫焦尼》,感人至深,卻又不動聲色。童話《去年的樹》寫生離死別,給人的感動是“哀而不傷”。中篇小說《月牙兒》是一個大大的哀傷,大大的哀傷之上,還要加上一個大大的感動,但是,它們並沒有像一塊大大的石頭那樣,沉重地壓在我的心頭。奔涌的淚流過后,心裡卻有一種莫名的暢快之感,想要緊緊地擁抱自己所擁有的當下生命。這些舉重若輕的作品,呈現的都是輕逸之美。
在兒童文學的四個美學特質中,稚趣之美幾乎是兒童文學的專利。“稚趣”與“童趣”庶幾相近,卻有微妙不同。如果說“童趣”主要指的是兒童的情趣,那麼“稚趣”“稚拙”則體現著一些童心未泯的成人的審美趣味。兒童文學的“稚趣”包含著幽默,但是與《堂吉訶德》《阿Q正傳》等成人文學的幽默不同,《小淘氣尼古拉》《我和小姐姐克拉拉》這些兒童文學的幽默都與兒童的心理和生活有關。我們看馬克·吐溫的一段經典描寫——湯姆因姨媽的誤解而受了委屈后,“他知道有一種渴望的眼色屢次透過淚眼落到他身上”“可是他偏不肯表示他已經看出了這個”“姨媽會多麼傷心地扑到他身上,像下雨似的掉眼淚,嘴裡不住地祈禱上帝把她的孩子還給她,說她永遠永遠也不再打他罵他了!可是他卻冷冰冰地、慘白地躺在那兒,毫無動靜——一個小小的可憐虫,什麼煩惱都結束了……他這樣玩弄著他的悲傷情緒,對他簡直是一種了不起的快樂”。
對兒童文學來說,稚趣之美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它既不是一種為了博讀者一樂的噱頭,也不是為了增色的一種點綴,而是一種十分本體的精神和品質,它蘊含著人生的智慧,朝向生命的樂觀、至性達天。
在兒童文學研究之中,“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存在分野,這是一種普遍而具有主導性的意識,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淡化甚至消解這一意識,學術研究就有可能步入歧途或陷入泥潭。但是,也需要承認,在某些特殊的語境中,“分野”意識也會暫時消失。比如,在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期,兒童文學一再被作為“新文學”來強調。胡風這樣評價中國兒童文學的開山之作《稻草人》:“五四運動以后不久出現的《稻草人》,不但在葉氏個人,對於當時整個新文學運動也應該是一部有意義的作品。”在胡風的論述裡,《稻草人》與《狂人日記》這樣的成人文學具有“一體性”的關系。再比如,在中國兒童文學呼喚“文學性”回歸的20世紀80年代,“兒童文學是文學”這一被廣泛論述的命題,強調的是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藝術共性。
侯世達和桑德爾在認知科學的巨著《表象與本質:類比,思考之源和思維之火》中指出:“人類認知的靈活性,就取決於在抽象階梯上上下移動的能力。因為,我們有時需要作出細微的區分,有時又需要忽略差異而把事物混在一起。”因此,討論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是否存在分野這一問題,要防止簡單化、絕對化,避免走入非黑即白的教條誤區。 (作者:朱自強,系中國海洋大學講席教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