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邃的歷史感 鮮活的畫面感
——話劇《北上》觀后

話劇《北上》劇照。 尹雪峰攝
《北上》是一部內容與形式各領風騷又有機融合的話劇。它讓我們領略到了舞台藝術特有的魅力。
要說清楚這部話劇,可能先要從徐則臣的長篇小說《北上》說起。也許在多年以后,有人會將《北上》這部長篇小說讀成一部歷史——關於中國大運河的歷史。我們能想象,徐則臣在寫這部長篇小說之前,做了多麼詳細的考察工作和田野調查。那些寫運河史的史學家們,也許付出的精力比徐則臣還要多。他們看了許多歷史記載、面對了許多有關運河的文物,但是徐則臣感應歷史的方式與史學家們大不一樣。他感應歷史的方式,是一個文學家的感應方式,與史學家們的興趣點、關鍵點也不一樣。
一部寫個人經驗的小說,也可以呈現出豐厚的、博大的集體記憶﹔一部虛構的文學作品,也可以呈現出堅不可摧的歷史真實。這大概是小說存在的理由之一。
那麼,話劇《北上》是否延續了小說體現的歷史精神呢?我以為是延續,並且很好地延續和發揚光大了。杭州話劇藝術中心選擇《北上》進行改編的原因,大概其中也有這一點:作品的歷史感。劇中,從杭州到揚州,從揚州到淮安,從淮安到聊城再到通州,我們看到的既是船的航行路線,又是歷史演進的路線。小說深邃的歷史感,原先在文字裡,現在在舞台上,在燈光裡,在造型裡,在表演中,相對於小說而言,“歷史”變得更加直觀。
從這個意義上講,話劇《北上》已經不再是小說《北上》。
我們大概都注意到了這部話劇別具一格的架構:它既有豎線,又有橫線,既在從前,又在現在——從前與現在經常是在同一個時間內於舞台同一空間中進行的。它們彼此是獨立的,但又是相互呼應的。
這樣一種架構方式,也是吸納了小說的結構。小說《北上》寫的是一條蜿蜒中國南北的河。寫河流,很容易就會“順流而下”,按河流的流淌方式,將作品搞成一條河的架構。順時序、順空間前后,這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徐則臣打破了我們的預測。小說時間從1901年一下子跳到了2012年、2014年。當我們以為它要成為河流架構時,它又跳回到1901年,甚至溯流而上,到了1900年,最后又寫到了2014年。正是這種別出心裁的架構,讓我們讀出了歷史的千回百轉、人世間的悲歡離合。
記得2019年,原著小說《北上》研討會上,我曾說:“這種安排,是否有值得我們探究的意味呢?但至少構成了一種閱讀的魅力。”加之敘述人稱的改變,我們不住地猜測這些人物之間的關系和來龍去脈,我們一定會有人世無常卻有常的感嘆與對命運的哲學思考。
通常,我們會說,小說是一門說事的藝術,哲學是一門說理的藝術。但,我另有看法:小說完全可以說理,關鍵不在於說,而在於怎麼說。小說本就應該給人“理”:人生的理,生活的理,事物的理,天地的理。小說《北上》離不開這些自然流淌在字裡行間的理。書中有很多精彩的富有哲理的句子,它們順理成章地鑲嵌在行文中,使這部小說變得厚重、富有力度,還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話劇與通常的小說相比,它不僅是說事的,還是說理的,而且后者有時比前者更重要。在話劇《北上》中,我們已經充分領略到了這一點:四周一片寂靜,眾多人物似乎都處於靜止狀態,而隻有一個演員富有感染力的長段獨白,有力地震撼著觀眾的心靈。
話劇的說理會使劇場籠罩著理性的光芒,而在“肯定之否定”的雙方對峙中,那“理”就像反復打磨的劍,越來越亮,越來越鋒利,結果就是觀眾被“理”征服。而舞台獨白,其實也是在“肯定之否定”中進行的,我們在話劇《北上》中完全可以感受到這一點。說理之所以極富感染力,還因為它的說理總是與情聯系在一起的——無論是小說還是話劇,其實都與情有關。
話劇《北上》驗証了“形式即內容”的論斷。這是一部充滿形式感的話劇。它改變了我從前看《櫻桃園》《茶館》等話劇的記憶。一個舞台,在形式上變化萬端,讓人驚嘆。旋轉的舞台,或升或降的船——那船本身就富有形式感。在背景幕上徐徐降落的角色名字、燈光、布景、道具,舞台上的一切,莫不具有形式感。但觀眾喜歡,因為這些都是“有意味的形式”。當那隻飽經滄桑的船在舞台上徐徐上升,最終定格於空中時,一個詞在我心中升起:永恆。小說是時間的藝術,戲劇是空間的藝術。一個有限的舞台空間,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北上》的“畫面感”,是我個人話劇欣賞經驗中感受最為鮮明和深刻的。它數次讓我想到了繪本:我寫了本子,而那個畫家——當然是一個出色的畫家,在完成插畫時,絕不是對文字的解釋,而是再創作。徐則臣的小說與話劇在舞台上的展示,非常像繪本中文字作者與畫家的關系。那些畫面,許多是徐則臣小說中並沒有的,他只是寫了一句,並無具象,但現在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卻是話劇中生動的畫面。
觀看話劇《北上》,我領略到了庄嚴。所有演員演出的認真,包括那些負責燈光、舞美等人員的認真,讓人肅然起敬。期待日后,話劇《北上》經過進一步修改、潤色,成為中國當代戲劇史上一部具有經典性的作品。(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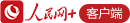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